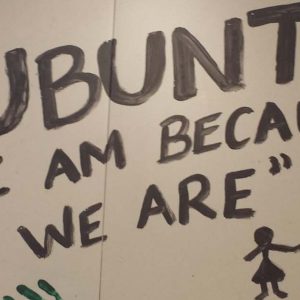“文化”一词的多义性与拉丁语动词colere的丰富含义相关,意指耕种田地、关心照料或修饰自己的身体、保护、居住、实践一种美德或从事研究,但也有敬重、对某一神灵或圣地的敬拜等意思。因此,在拉丁语系语言中,农业、文化(习俗和知识)及宗教和民间“敬拜”之间密切相关。其中始终贯穿着的一个意念是谨慎细心并谐和地关护土地、管理土地的权力、居住于大地上的人,以及我之为我和我为修身养性而必须耕耘的“心田”[1]。
当然,这一概念在不同语系中具有不同的共鸣。在汉语中,“文化(文学)”这一概念中的“文”主要是指对符号的观察和了解,首先是天象,然后是文字符号。“教”字指的是一种教导,一种学说,后来也指一种宗教,并用于“教化”这一概念。栽培耕耘之事主要以“耕”字表达。然而,儒家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孟子(约公元前380-289年)强调了“深耕(发展)”与“修孝(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2]。在所有中国典籍中,“农”、“礼”、“德” 整体的三要素,对其中任何一个元素的忽视都无法使另外两个方面得以保全[3]。
谷物栽培对社会和仪式的塑造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栽培以谷类作物为主[4]。当然,豆类、油料作物或块茎栽培所提供的食物来源也关乎做事方式、世界观、神话、记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伦理道德(ethos)依据。但豆类及小部分油料作物往往是与谷物相关的作物,受谷物发展的带动。最重要的是,人们只要说出“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些词,就能意识到这些主要谷物与主要文明综合体之间跨越千年的关联程度。此外,小麦、大米和玉米还有数量惊人的“同系物”,包括大麦、高粱、燕麦、黑麦、小米、福尼奥米(fonio,白色或黑色)、苔麸(teff)、薏苡(lacrime di Giobbe),等等。此外还有所谓的“假谷类”,如藜麦、籽粒苋或荞麦[5]。现在,谷类和假谷类的基因特征都已被人类劳动所改变,以至于变得依赖人类:人类和谷类已经共同进化,可以说,两者已经相互驯化了[6]。
由于其营养价值显著,且易于储存和运输,谷物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们的驯化,它们在栽培、烹饪方法、食用以及造酒中的使用之改良,它们的秸秆的用途,总之,有关它们的一切已经并仍然对人类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和政治机构的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东地区收获野生谷物的最早确凿迹象可以追溯到大约23000年前[7],甚至更早[8]。大约在1-1.2万年前,他们的作物开始被驯化;然后这些驯化得到发展,尤其是当种子和各种知识开始传播和交换时,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被彻底改变,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对这种作用的意识。
对于以往从事谷物栽培的人民来说,它既是一种奴役,也是一种进步和技术转移(施肥、灌溉、储存、机械化、研磨、烘烤等)的持续。耕种所造成的农奴制不仅源于农民不得不将自己束缚在一块土地上的事实,而且也源于为播种准备田地、为灌溉进行水利工程、组织收割和周而复始的年度周期的需求:所有这些需要都为强权者施加的胁迫做准备,而强权者又反过来进一步深化这些需要。劳动分工通常以性别、工种、社会阶层、算术、文字记载、税收[9]等为依据,而每一项这些制度的起源至少可以在部分程度上追溯到向谷物栽培的过渡[10]。
谷物也被证明是一种首要的礼仪和宗教载体: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丰收季、播种时为辟邪或免受蝗灾而念诵的祈福神咒,或是在宗教庆奠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谷物制品。圣体圣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安第斯群体举行的祈雨仪式展示着植物和其他生物之间所寻求的休戚与共。插秧所需的农家互助会体现在农忙时刻,并同时通过集体活动改变自然的歌声得以表达。纪念亡人节(día de los muertos)、圣体圣血节以及儒家的祭祖都在过去或现在赋予年度大事以庄严意义。谷物的生物周期赋予我们的事农祖先的生存以节奏,并将其嵌入共享意义的网络中:播种是出生;耕种土地是学习过程,是奋斗;开花是结婚;收获是死亡,同时也是幸存;种子的生成是分娩;稻草因其用途而暗示着避难所和保护;研磨和烘烤是转化、重生或转世;酒(很早便通过谷物发酵而制成)是兄弟情谊的载体,也是与神灵沟通的载体。
于今的一个重要欢庆
难道我们只是在这里谈论过去吗?那些已被技术远远抛在时代后面的农耕社会与文化是否值得缅怀?沉浸于历史上建立的文明综合体的“谷根”不仅是一种纪念行为,而更是一个认识它保存至今的原始功能的问题。这种认识涉及到谷物这种生命表现形式的隐性或显性表述,它与土壤和生命的关系,它与制约我们的故事、信仰及做事方式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反思那些或者会在我们的社会中消失,或者更有可能会在继续存在的同时发生转变的事物。这在我们正面临一场人类与各种形式的生命之关系陷入普遍危机的今天尤为重要。并非所有的危机都是“世界末日”,但这个词的使用至少表明了一种需要突破性反应的转折。在人类与生物的关系中,这种危机的系统性特征要求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社会复原力和自然环境复原力具有一个相应的全面了解。
在非常不同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下,人类以往思考、进行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进行粮食种植的方式都具有道德和灵性价值,并通过伴随这种耕种的实践和仪式得到表达。正如琐罗亚斯德教的一篇文章所言,“播种谷物的人播种正义”[11]。人们可以假设一个谷物栽培的“道德功能”:它无疑促成了祭祀活动的道德化或人性化,尽管谷物是生物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在礼仪中的使用继续引起关于祭祀义务终极原因的疑问。在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中所展开的对第一个盟约祭献的考虑,就像保禄在格林多人前书中对圣餐之伦理及其共融性的思考一样,证明了在仪礼中使用谷物帮助人们领悟到祭祀义务的终结,并以一种新的与神沟通的方式取而代之。
禁食和欢庆:生存之节奏
谷物仍将是人类营养中的一个基本元素,它可能是不可替代的,尽管其消费可能会遵照比以往更为周到的营养组合。这与重大的社会挑战同步:农业必须养活世界人口,为此,必须为其生产者提供收入和途径,以保护地球上的土地。农业生产者已变得为数甚少,他们所从事的不可或缺和“生命攸关”的活动必须得到相应的认可和报酬。在各大洲保持最低数量的农民,同时保障围绕各种农业系统组织的知识及其传播,是对人类未来的保证。此外,我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我们共进餐食或是过于频繁地独自进餐的方式,无论是对营养、环境,还是对道德和文明都有所影响:谷物、仪礼和知识将不断发展,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将继续共同发展。
传统农业社会的逐渐消失,无疑使基于谷物发芽或收获的隐喻在今天的意义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和令人回味。同时,谷物生产和消费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存在方式,对这些符号进行了重新加工和解读。例如,对基督信仰传统来说,“圣体圣事渗透的生活与生存中的重要事项相关联:面包与饥饿、食物与快乐、食品问题与全球食品政治、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12]。今天,人们对食物来源和质量以及革新消费模式的新关注重新唤起了古老的形象联想,刺激了谷物成为“圣物”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同分享的餐食总有圣事幅度的内涵;而掰饼一类的行为,或是因为其粘性代表社群和跨代团结而分享玉米啤酒或吃糯米饭,则清晰表明并庆祝共享餐食中可能拥有的圣事性的力量。
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了解斋戒和欢庆、歉年和丰年的交替。毫无疑问,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交替随着过去半个世纪的文明变革而淡泊。然而,必须牢记的是,食物的特点是一种或多或少的丰富与匮乏的交替,而且每一种食物的同化都是通过“意义”的交流、通过与自己以及与群体和神灵关系的持续进行而得到促进。此外,“禁食现在被医学视为能够为身体和健康提供一种间歇,以便通过理性安排的合理实践,提高思想和身体上的自制能力。[……]人只有在了解自己的身体并能对它的偏激加以自律的时候,才能达到精神上的自如”[13]。禁食是对我们努力掩饰的有限性的一种提醒。
但是,文化、传统、宗教并不只关乎禁食,也关乎与饮食、丰盛和分享紧密相连的欢庆。欢庆及其典型的有节制的过分以一种(理想的)大快人心的方式庆祝生命和群体的延续以及对生存所需资源的征服和分享。主食,即谷物,在那里找到了它们所有与心灵和感官快乐相关的崇高维度。如果仔细观察,在我们的城市化社会中,狂热消费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当失去禁食和欢庆相交替的意义和节奏时,也就无法再保持平时应有的适中。日复一日的强制性丰盛已不再是欢庆,而是一种负担。
如果全球挑战继续恶化且更加令人痛苦,正如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危机以及当前乌克兰战争所引发危机的无情展示[14],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学会庆祝并宣明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分担的哀恸,我们已确立的休戚与共,我们的战胜严冬?只有如此,禁食和欢庆的平衡,就像与其相关的食礼一样,才能找回它那只是在一段有限时期内被隐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播种与收获,饥荒与丰收,危机时刻与耐心等待的季节……沉醉于虚拟社会但重新发现自己的生命力并因此而无比脆弱的我们,始终无法摆脱谷物的节奏:它为我们的生存过程悄然地打着节拍。
- 本文总结了下述书籍中所提出的一些主题:A. Bonjean – B. Vermander, L’ Homme et le grain.Une histoire céréalière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21。这部作品描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与谷物栽培有关的遗传、技术和礼仪方面的进步和交流,并且从当今引人深思的科学、社会和思想转变出发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 ↑
- 参阅Mencius IA5. ↑
- 然而,这种关系的表达方式有别于共和时期的罗马: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中国将领会像辛辛那提斯(Cincinnato)那样返回自己的田地耕种。早在古代中国,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社会和空间划分即已非常严格。同时,对政治和道德堕落的抗议通常以还乡务农的生活方式表达:参见孔子《论语》18.6和18.7,以及《老子》(又名《道德经》)的许多段落。 ↑
- 谷物以固体或液体形式提供人类营养中约50%的能量供应;其产量的35%至40%用于动物饲料;用于生物燃料生产中的谷物正在增长。小麦、玉米和水稻目前占谷物产量的90%以上,其中玉米在饲用和工业用途中占最大份额。 ↑
- 这些植物虽然不像谷类那样属于禾本科植物,但也会结出种子,可以磨成面粉。 ↑
- 关于人类如何影响并继续影响其他动植物生命形式的生物进化之概述,可参阅B. Shapiro, Life as We Made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1. ↑
- 参阅I. Groman-Yaroslavski – E. Weiss – D. Nadel, «Composite Sickles and Cereal Harvesting Methods at 23,000-Years-Old Ohalo II, Israel», in Plos One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67151), 23 novembre 2016. ↑
- 参阅R. G. Allaby et Al., «Geographic mosaics and changing rates of cereal domestication», in Phil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2 (1735) (https://doi.org/10.1098/rstb.2016.0429), 23 ottobre 2017. ↑
- 谷物由于计算和运输的便利性而成为受人青睐的税收工具。 ↑
- 关于这种通过谷物种植实现人类自我驯化的机制,可参阅J. C. Scott,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然而,查阅此书时需注意:其精辟见解并不排除某种系统主义,以至于有时会影响到对所介绍的事实的选择和阐述。 ↑
- Avesta, Vendidad, Fargard 3, v. 239. ↑
- A. Bieler – L. Schottroff, The Eucharist. Bodies, Bread, and Resurrec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7, 127. ↑
- D. Gaurier, «Les interdits alimentaires religieux: quel possible rapport avec une forme de sécurité alimentaire?», in F. Collart Dutilleul (ed.), Penser une démocratie alimentaire, vol. I, Costa Rica, Inida, 2013, 6. ↑
- 根据经济复杂性观察站(OEC)的 数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出口量总额中所涵盖的比例为:小麦近30%,玉米14%,葵花籽油72%,葵花籽15%。严重的供应问题迫在眉睫,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