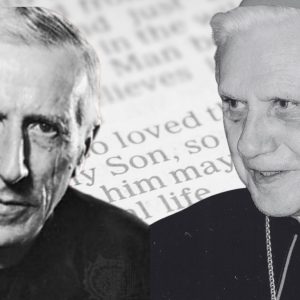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言语中凸显强烈邀请教会上下走同道偕行之路。他更尝试以亚马逊区域和以家庭为主题的两个主教会议为蓝本,将同道偕行打造成一个形象。我们在本文扼要回顾(主教)集体领导(collegialità)和同道偕行(sinodalità)长远历史的意义之后,愿意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意象(immaginario),作为建立这个形象的基础。事实上,今天我们缺乏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定义的新的“社会意象”(immaginario sociale)。
在梵二大公会议激起热烈讨论的诸多问题中,或许没有一个像全球主教集体领导(collegialità episcopale)这个议题这么受到议论。教会历史学家约翰·奥梅利(John O’Malley)说:“主教集体领导议题像避雷针一样,承受了大公会议的紧张局面。没有任何一次大会、没有任何一道文献像《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第三章那样遇到如此重大的争论或受到如此严密的检讨。在大公会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该章之后,问题仍然没有止息,甚至到最后关头还发布了著名的“奉最高当局命令”的“预先说明书”(Nota praevia)。大公会议少数但深具影响力的与会教长不顾情面猛烈反对主教集体领导,…指出有某种比订正或发展更为重要的事深陷危急”[1]。
那么世界主教集体领导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使这个议题变得如此具争议性?为什么会产生争论?
世界主教集体领导的意义
出席梵二大公会议的主教和神学家们都深知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1870)曾仔细审查了教宗的权威,却没有时间考虑主教们在教会中或在教宗面前的身份地位。这项未完成的工作有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给教会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平衡的教会学(ecclesiologia)。显然,这是个必须予以面对、却也是困难重重的问题。事实上,梵二第一阶段会议(1962年10月)有关礼仪使用通俗语言的辩论确定:礼仪使用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之事,该当只由梵二教长们所界定的“地区性的主教团职权当局”来决定(礼仪宪章22),也就是说由使用特定语言的国家或地区的主教们来决定。但哪一种机构应该作这类决定或该当如何运作这件事,直到开始讨论有关教会的文献《教会宪章》为止,仍未厘清。
梵二第一阶段会议否决有关教会文献的初稿之后,在第二阶段会议(1963年10月)中举行了一次意见投票,藉以确定梵二有关主教团集体领导的立场。投票中有84%的主教赞成“主教团继承宗徒团,这样的团体在与其首领教宗连结之下,对教会内享有完全和最高的权柄”[2]这个立场。于是以这样一段话开启了走向文献最终定稿之路:“由于主的规定,圣伯多及其他宗徒们组成一个宗徒团。基于同等理由,继承伯多禄的罗马教宗和继承宗徒们的主教们,彼此也连结在一起。按照很古老的一种风纪,设立在全世界的主教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罗马主教之间,经常在统一、爱德及和平的联系之下,息息相通;同样地,他们召集会议,衡量大家的意见,对重要的问题做共同的决定,这些都说明主教圣秩的集体性质;历代的大公会议也清楚地证实这一点”(教会宪章22)。
随后,梵二与会主教们在最后阶段会议颁布的《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中也强调这个概念说:“主教因受圣事的祝圣,及与团体首领及其他团员的圣统制内的共融,成为主教团的成员。‘主教团在训导与牧权上继承着宗徒团,而且就是宗徒团的延续,只要与其首领罗马教宗在一起,则对整个教会也是一个享有最高全权的主体:然而,这种权力,没有罗马教宗的同意,不能使用’(教会宪章22)。这样的权力‘以隆重的形式,施行于大公会议内’(同上)”(《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4)。
主教们随之祝望成立一个组织机构,经由它,“从世界各地,按照罗马教宗所定或将定之方式与办法所选之主教,对教会最高牧者在咨议会中贡献有效的协助,称为主教咨议会。此一会议既代表全世界主教,同时亦表示全体主教,在圣统的共融中,共负关怀整个教会的责任”(《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5)。
梵二大公会议究竟要肯定什么?依我们看,有两件明显的事。首先,主教们,一如最初的宗徒们,形成一组人,一个团(collegio,这个字在拉丁文collegium中意味着‘一些人结合成一体,一个社会,一个社团’);所以主教们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宗徒们有“十二位”,这只是个象征性的数字,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天主到最后必会把他们聚集成一体。因此,主教们被“统一、爱德及和平的联系”所维系:“世界主教团是以教宗为元首,以主教们为成员,藉圣事的祝圣,和在圣统制内与该元首及其他成员的共融而组成,在世界主教团内,宗徒团继续存在;该团与元首在一起,而总不与其分离,便是普世教会最高全权的主体”(天主教法典336条)。正如美国神学家理查·盖拉德兹(Richard Gaillardetz)强调的,“这项大家都接受的对普世教会的权力和权威的肯定,代表着世界主教集体领导这项训导的核心”[3]。
其次,主教集体领导的行动在初期教会中已有他们举行公议会或主教会议的传统例证,他们举行公议会,“就重大问题表达足以反映许多人的意见的共同判断”。在梵二大公会议中,与会教长了解到主教集体领导乃是教会主教会议或大公会议传统的延续,所以并非什么新鲜事,而是教会全体主教团结一致的表现。有关信仰和教会纪律的重大问题都由主教们集体来决定,他们“与伯多禄在一起,而总不缺乏他”,而不是由某一单独教区的主教个人做决定。
梵二大公会议的意向可从议程辩论中的一些发言和当时神学家们发表的书面文字中窥探到。比方说,东方礼梅吉德(melchita)教会宗主教马西莫四世塞赫(Massimo IV Saigh)提及东方礼教会常设主教会议(sinodi permanenti)的经验,并建议将之作为普世教会的模式,于是有五百多位主教联署致函教宗,要求设立世界主教会议(sinodo)[4]。同样地,在当时一次曾激起许多争论的会议中,神学家若瑟·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推崇初期教会区域性主教会议集体领导的流畅观念,他说:那是教会共融的表征(communio Ecclesiarum)[5]。所以,在梵二大公会议的思维中,在教会内罗马教宗的职务和主教治理教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在《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第三章中,已明确指出这个关联说:“从教会的初世纪,管理个别教会之主教,由于兄弟友爱的共融及宗徒传教使命所推动,即已同心合意,推进公共及个别教会的利益。故此,召开教区会议、教省会议及全国会议,主教们为各教会,订立了为传授信德真理及整饰教会纪律的共同原则。本届神圣大公会议,希望教区会议及其他会议悠久制度,恢复其能力,以更适宜、更有效地在各教会中,依照时代情形,增加信仰维护法纪”(《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36)。
梵二大公会议这道法令接着指出,这一切在当今都必须化为主教会议(conferenze episcopali)的形式,并希望在尚未存在这些会议的地区予以成立,同时制定各自的规章。主教们的意愿已经很清楚而直接。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引发如此的争论?
梵二大公会议内的反论
自梵二大公会议汲取灵感的初期教会到我们今日之间,从中世纪起即有强有力和以教廷为中央集权的教宗职权体制(papato)介入期间。教会历史学家理查·少仁(Richard W. Southern)说:“在这整个时期,从贝达(Beda)到路德(Lutero)时代,从第八世纪教宗权威实际接管西方世界到继之而起的帝王权威,乃至十六世纪帝王权威的支离破碎,从东欧和西欧政治联系的决裂到旧大陆闯入辽阔的西方海外世界为止,教宗职权体制始终是西欧的主导体制”[6]。
在那几个世纪,教宗的统治地位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其上升的原因有许多,仅举出几个例子:由于罗马是伯多禄和保禄殉道之地,因此给予这个城市的主教重要的首席地位;由于罗马帝国迁都到君士坦丁堡以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所造成的真空状态;几位教宗奋勇抵抗蛮族的入侵和饥荒与瘟疫的蔓延;第七世纪伊斯兰的崛起打断了罗马与古代的宗主教区亚历山大、安蒂约基亚及耶路撒冷的往来接触;最后就是几位教宗,不一定有根据,坚称自己对其他地区的教会以及对俗世拥有首席权。然而宗教改革运动反对这些教宗的类似要求,以致打破了西方教会的共融。虽然如此,罗马(教宗)仍然坚持立场,益加强调自己的权威,并于十九世纪达到巅峰,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中宣布教宗不会错误为信理。
梵二大公会议与会的主教们深知过去这段历史,所以并没有否定或反对(教宗不会错误)那个训导。的确,他们在《教会宪章》第25章重申这条信理,但以世界主教集体领导和主教团不会错误的观念予以平衡。不过为数仅占与会教长16%、却具影响力的少数主教们担心这或将限制教宗的权威和特权(犹记得上次投票中,有84%的主教赞成全球主教集体领导)。基于这样的局势,梵二大公会议便设法克服主教们与教宗之间的对立,将教宗置于世界主教团内,作为元首。但在那少数主教看来,这似乎缩小了教宗领导普世教会的职权。为了免除少数主教的担忧并使之积极参与其事,保禄六世教宗在最后时刻(令大公会议秘书长)附上﹤预先说明书﹥(Nota esplicativa previa),藉以说明主教集体领导不应被解释为企图限制教宗的首席权。
大公会议或主教会议的传统
在教会内,主教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唯一的团体(身体)并不是什么新意。文献记载在第二世纪已有主教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地方性会议,为处理威胁教会秩序和规律的问题,如确定巴斯卦节日期等。后来那些会议成了“教会生活的规律和不可或缺的特征,是地方感恩祭团体凝聚成普世教会团体的正常体制表现”[7]。就如所知的,从第二世纪中叶到大额我略教宗(590-604)之间,就举行过四百次以上的主教会议和集会。比方西彼廉(Cipriano)和奥斯定(Agostino)就参加过许多次北非的公议会,而奥斯定这位伊波那(Ippona)的主教为了反驳多纳特主义者(donatisti),也曾在会中认定公议会法令并没有与圣经相同的权威。
这种主教集体领导的经验存在于多种层次: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和普世性的。尼西第一届大公会议(Il I Concilio ecumenico di Nicea ,325)颁令称:“每个教省每年宜举行两次主教会议”,每位主教必得参与,而那时期的每位教宗也都鼓励举行这样的集会。且不论随后是否如此进行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那些会议显示在那时刻整个教会的期待。
这个公议会或主教会议的传统不但没有因为初世纪教会的过去而终止,而且继续成为教会决定有关事务的形式。此外,这个传统表现了各地方教会的团结一致,它们认为这是“共融中的共融”。基督教会各地所有的团体都承认最初七届大公会议颁布的法令的权威,直到公元787年举行的尼西第二届大公会议为止。另有许多即使不被认为全体主教会议或大公会议的地方性或区域性主教会议和公议会,它们的决定有时也被接纳为整个教会传统的一部分。
总之,当教会慢慢地越来越与中古世纪社会整合成所谓的“基督信仰世界”(cristianità)后,大公议会开始被世俗的执政者或有权势的家族所操纵,比方在罗马就是这样。这些大公议会不再是仅由主教们参与的会议,而是让世俗政权的代表也参加。教会历史学家克劳斯·夏兹(Klaus Schatz)指出:“基督信仰第一千年代中教会的各届大公会议都仅是主教的会议,通常由皇帝主持;但中世纪的大公会议则非单纯的教会会议,而是基督信仰世界的会议,由教宗主持”[8]。于是,主教会议(sinodi)落入政治手中,多少违背了它们的本质和目的。第十一、十二世纪额我略七世教宗着手进行的改革旨在恢复教会独立于世俗掌控之外。
随着十四、十五世纪因为有两位、甚至在某个时候有三位角逐教宗职位者,而导致西方教会大分裂之后,大公会议的传统终于复苏,重拾活力。为了解决那件丑事并重建教会的合一,曾举行过几次大公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康斯坦茨(Costanza)大公会议(1414-1418)。这次大公会议在它颁布的著名法令﹤Haec Sancta (此神圣的)﹥中声明此会议的权威直接来自基督,因此有权利做为裨益教会所需要的事,包括最严重时可以罢黜一位教宗。蕴含这项声明意义的神学在指出教会就是信友的团体,亦即最后的权威所在就是教会团体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概念的基础就是保禄宗徒所指出的基督奥体的形象。教会被视为以地方教会团体为起点的一连串集会;之后,这个教会逐渐汇集成一个教区或教省,诸如古代的宗主教区;最后就形成如基督的奥体普世教会。所有这些地方教会团体以地方性的主教会议、区域性的公会议为其代表,而整个普世教会最后由大公会议代表之。
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以罢黜竞争教宗权位的对立者,并于1417年选出新教宗玛尔定五世(Martino V)而结束当时教会内部的分裂。这次大公会议也颁布﹤Frequens(经常)﹥法令,规定未来每位教宗每五年、之后改为每七年、后又成为每十年得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于是有了随之而举行的帕维亚(Pavia)、锡耶纳(Siena)、巴塞尔(Basilea)、弗罗伦斯(Firenze)、乃至拉特朗第五届(Lateranense V,1512-17)等大公会议。1517年马丁路德以发布﹤95个论题﹥开始他的宗教改革运动(La Riforma)。很快地他又要求召开一次“自由和公开的大公会议”以解决问题,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位教宗托故搪塞,他们担心召开这样的大公会议可能招致的后果。最后,迫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arlo V)之逼,保禄三世教宗终于召开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63),但这位教宗对大公会议的忧虑仍然存在,而那支持他的人也认为(召开)大公会议的看法要不是异端,至少乃是误入歧途。
虽然仍有一些类似的企图,就如英国历史学者弗兰西斯·奥克利(Francis Oakley)所称的,设法促使“由体制所支持的遗忘一切”(un oblio sponsorizzato dalle istituzioni),但共融的神学或称教会会议的概念,仍继续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延续[9],这在十六世纪英国圣托马斯·摩尔(san Tommaso Moro)和理查·浩克(Richard Hooker)的写作中,在十七世纪保罗·萨尔比(Paolo Sarpi)的作品中,尤其在他回复罗伯托·博敏(Roberto Bellarmino)的文字中,还有在埃德蒙里切尔(Edmond Richer)的书写中可见。这也是巴黎大学神学院官方教会学的观点。但出现在由贾克·贝尼涅·布瑟(Jacques-Bénigne Bossuet)主教主笔、于1682年由法国全国神职人员大会所采纳的“高卢四条文”(Articoli gallicani)[10]中的主张最为持久和最具影响力。这四条文被写入1801年拿破仑与庇护七世教宗签署的协定中,前者并命令在法国的每位神学教授必须予以讲授。同样的观点也被十八世纪德国的费布罗尼乌斯主义(febronianismo)和奥地利的若瑟主义(giuseppinismo)所重申。这种在教会内由会议或主教会议领导治理的观点复由法国巴黎大学神学院院长亨利·马雷(Henri Maret)和数位法国主教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中提出来。显然,在这样的场合类似观点无法占优势,这也因为世俗力量或某些国家政府的阻碍所致。
我们之所以提到教会会议及主教集体领导概念的历史,就是为了强调在梵二中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新奇的事,而是回到源头(ressourcement)。再者,十四、十五世纪出现的主教会议或大公会议运动的目的乃在拯救教宗的职权,而非将之窒息。从十九世纪起,教宗在主教之上以独特的方式行事已成为众所熟悉的主导观点,但这个观点已与教会更具会议性的自我认识(autocomprensione più assembleare)共存。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并不、也不应该被视为对立。然而,它们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依旧长久持续,即使两者在梵二大公会议中并存并列,也没有获得解决。
对今日教会的意义
一如我们所提到的,梵二大公会议教长们清楚表示,“希望教区会议及其他悠久制度会议恢复其能力”(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36)。
我们生活的世界已进入全球化和后现代化。这两个现象非常广泛,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无意过于进入细节,但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共同的特征[11]:1)科技加速了交流和流动,使我们更意识到文化的不同和多元化;2)在一个地方发生的诸事都会影响到许多遥远的地方;3)地方和全球、局部和普世都存在辩证的关系;4)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出现日渐增长的区域化现象;5)国界越来越容易渗入,国家对边境的控制趋弱;6)虽然在文化上有些表面的共同,但差异和本位主义却又重获肯定;7)许多地方大力推动减少中央集权对地方决策的干预,更加期待参与、民主进程、对话和彼此尊重;8)最后,赋予妇女和少数族群更多的尊严和权利。
尽管类似的一些社会和文化内涵也隐含在梵二的文献中,但如今这些思想观念已变得越来越清晰有力。这一切都指出教会必须具备相应的体制结构,以利对话和咨询,承认区域和文化的差别,增进各地教会的交流,但保持普世教会的合一。主教会议和大公会议就是在基督信仰团体内把这一切承担起来的历史性形式。
从梵二大公会议开始,平信徒日益体认到他们是天主的子民,而教会也需要他们领受的恩典。男女教友在教会内负有更多的职责,在学校、医院、监狱、本堂区和传教地区肩负领导的角色。他们在教区办公室、在修院、在神学教育、在教学和研究领域担任职务。
一个新的社会意象
在历史的逐渐演进中,教会采行并适应环境文化的社会政治形式。比方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教会根据帝国行省的体制组织起来,并仿效帝国元老院议事的方式于公元325年在尼西(Nicea)召开第一届大公会议。在封建时代,教宗颁赐给主教和他的臣属采邑封地,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服从;而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手下的牧人。在君主体制时代,教宗身为一位绝对的统治者,由他的教廷人员和枢机主教们等等环侍着。
从十八世纪起,世界兴起更民主的生活方式,透过选举制度、分权、控制、均势以及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将最高权力还给人民。然而,教会并非民主体制,它不是建立在受管理者的同意上或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托马斯·赫伯斯( Thomas Hobbes)所认为的社会契约上。我们提过的主教会议或大公会议传统叫我们知道,教友虽然不是以“一人一票”的格式参与领导教会,但总有某种参与的形式。总之,在最近两百年来我们都习惯于生活在教会中央集权中,以致难以想象以不同的方式度基督信友团体的生活。或许今天在教会内已感到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意象”。
所谓“社会意象”,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是“个人想象他们社会存在的方式,他们与别人的存在彼此交错的方式,如何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期待获得正常的满足,赖以建立这个期待的最深概念和标准形象”[12]。这并不是说如此的社会意象已清楚确立或有意识地予以附和。这个意象只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中某个社会族群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了解自己的习惯和共同的举止。
或许在一个社会意象改变的时候更容易发觉这个意象。比方说:1)在北美,不论为科学界或为一般人士,致力寻求地球以外的智慧的计划,在今天已成为坚定的事实。这在五十年前并非我们共有的意象,今天则是如此;2)今天,许多国家都认为吸烟对健康有害,因此在餐馆、咖啡酒吧间和其他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但五十年前并没有这回事;3)五十年前,女性想都不敢想研读神学,现在则有可能。我们的社会意象已经改变了。
这样的改变也能发生在教会内吗?今天,“巴洛克式的社会意象”[13]似乎仍然活跃,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有一种普遍化的观念,这个观念根据先已安排好的、彼此尊严与价值并不相等的一系列的身份角色,一种圣统阶级制度(gerarchia),置个人于团体之下。在这样的社会意象中,“不平等”不仅具有其功能,而且还是必要的:这是宇宙本身不能改变的结构。这样的社会意象完全相反最现代的看法,这个看法推崇个人的权利,每个人享有基本相同的人性尊严和价值,也相信任何社会区别仅属于功用上的,所以总是可以改变的。现代的社会意象深信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并宣认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总统,也不在法律之上。且不考虑任何优劣,我们可以设想许多信友所感受的不满和失望都因不同社会意象之间的冲突所致。今天,在教会内,我们也期待教宗、主教、牧人和各权威当局怀抱同样的态度,一如我们根据正义及人人平等的准则,要求于社会和政治界领导人士的一样。
当然需要谨慎从事。解决之道不在于认为教会应该突然完全盲目地采行现代民主或国会体制的领导形式。我们都知道那些社会模式也可能出现弊端。所以,我们期许的就是希望我们在教会内的共同生活能够依循一种足以培育某些现代世界的良性价值、尤其知道汲取古代大公会议和主教会议传统的风格。梵二大公会议有关主教集体领导的训导就是邀请我们改变社会意象。1965年梵二大公会议结束之前,保禄六世教宗创立常设世界主教会议(Sinodo)就是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他接纳主教们的期待,但也重申教宗的特权。
在教会历史中,主教会议和大公会议采行过不同的举行方式,未曾有过固定和明确的模式,所以今天也没有理由采用统一固定的模式。基督信友参与决策的进程方式可以因地制宜。
教会传统上把职务分为主教、神父、执事三个等级,一如传统上赋给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职权,这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为了回应教会团体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即使执行的方式已有所改变,但一直保存下来。至今,教会仍没有改变对这种权威方式的需要。话说回来,若没有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的灵感和勇气,也不会有梵二大公会议。为此,当我们期望更新主教会议或大公会议决策的进行方式时,我们并无意唾弃这些职务,包括伯多禄的职务,而是愿意重新检视并恢复它们的关系,以符合主教会议的传统和遵循梵二大公会议的旨意。我们不能忘记参与十四、十五世纪大公会议的教长们意在拯救教宗的职权,而不在摧毁它!同样地,梵二大公会议所讨论的主教集体领导不在缩减教宗的道德权威,而在提升它。
从教会大公合一(ecumenica)的角度看,基督教会大公合一理事会(il Consiglio ecumenico delle Chiese)几年前公布的“教会的本质和使命”(La natura e la missione della Chiesa)文件[14]曾提出类似的建议。该文件就集体领导和大公会议精神(conciliarità)两个观念表明:“大公会议精神是教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它建基于其成员共同领受的圣洗(参见伯前2:9-10;弗4:11-16)。在圣神的引导下,整个教会不论是分散或聚集,都具大公会议精神。因此,这个精神临在教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大公会议精神业已临在最小地方教会团体成员彼此已存在的关系中”[15]。此外,上述文件的声明也承认:“每次某些人、一些地方团体或区域性教会集合在一起,为讨论并做重要决定时,总需要有人召集和主持,好安排妥当集会,支持促进、分辨和协调意见的一致”,而那些主持集会的人总必须“尊重地方教会的完整,为无声者发言,存异求同”[16]。为此,在世界层面上,某种全球性的首席形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恩典,而非对其他教会和它们作证特征的威胁”。这样的首席地位不反对大公会议精神,因为历届大公会议都肯定这个首席权的行使。
教会历史中的每个时代都应该深加思考主教身具的大公会议性质和其与教宗首席地位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梵二大公会议为我们当代努力设法做的事。我们能够也必须继续发展梵二大公会议本着耐心、勇气和希望开创的大业。
- J. W. O’Malley, «“The Hermeneutic of Reform”: A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ological Studies 73 (2012) 540. ↑
- R. R. Gaillardetz, The Church in the Making,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6, 18. ↑
- 同上,页77。 ↑
- 参见同上,页33。 ↑
- 参见同上,页35。 ↑
- R. W. Southern,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0, 26. ↑
- B. E. Daley, «Structures of Charity: Bishops’ Gatherings and the See of Rome», in T. J. Reese (ed.), Episcopal Conferences: Historical, Canon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7 s. ↑
- K. Schatz, Papal Primacy: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6, 79 (in it. Il primato del Papa e la sua storia: dalle origini ai nostri giorni, Brescia, Queriniana, 1996, 126). ↑
- Cfr F. C. Oakley, The Conciliarist Tradition: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Catholic Church 1300-18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 ↑
- 该四条文宣称:1)教宗对俗世事物没有权柄;2)在精神事物上大公会议高于教宗;3)法国教会所接受的法律不可违背;4)在信仰问题上,教宗的判断只有经过大公会议的批准才成为不可改变的。 ↑
- Cfr Th. H. Sanks,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ty and Governance in the Church», in Louvain Studies 28 (2003) 194-216. ↑
- C. Taylor, Gli immaginari sociali moderni, Milano, Meltemi, 2005, 6 s. ↑
- J. P. Beal, «Something There Is That Doesn’t Love a Law», in M. J. Lacey – F. Oakley (edd.),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in Catholic Moder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9 s. ↑
- 参见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Ginevra, Faith and Order Paper 198, 2005, 107. ↑
- 同上,26s。 ↑
- 同上,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