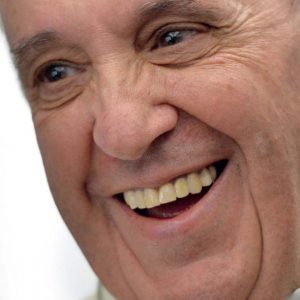我们所处的加速变革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伴随着许多生活领域中的危机。面对这种往往含有悲剧性的经历,人们会对我们的共同人性感到无言以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危机之中,我们的视野才得以开阔,从而发现一种对人类的新理解、重新归纳与修和,以至出乎意料的际遇才得以出现。与其是理论性的概括,我们更需要一种整体的智慧和“指南”,使每个人进入自己的人性之中。这正是葡萄牙枢机、圣经学者及诗人若瑟·托伦蒂诺·门东萨(José Tolentino Mendonça)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感到对一种更全面的智慧的需求,一种不仅以心智能力为基础,而且以我们的肉体和世界的整体现实为基础的智慧;根据这种智慧,对日常习惯或味觉等感官的反思不会被视为漂浮不定,而是能够使我们加深对自己的认识”[1]。
基于这一信念,一种新的神学方式与食品界的相关知识展开对话,希望通过源自基督信仰的人性化资源而构建这一共同智慧,这就是“美食神学”[2]。根据这种智慧型神学,以“美食”方式看待我们的人类现实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口,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当下。的确,从直接的意义上讲,美食与餐桌上的愉悦相对应,属于欢乐和无偿的范畴。在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已经属于反思的层面,它与“在饮食行为中构建快乐的知识体系”相对应[3];这涉及到一种有序的烹饪知识,即: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叙事、历史、口味及价值观。然而,这两个层面将我们引向第三个层面–也就是本文所关注的层面–当我们关注其词源学含义时,这个词的词素将会揭示:对美食(gastronomia,源于γαστήρ,gastér+νόμος,nómos,,即“胃,肚子” + “法律,规范”)的探寻可以展现内脏(viscere)所特有的规范性(normatività),为我们身体中的天生资质提供审慎的见证,但我们却往往对此不与讨论[4]。于美食神学而言,这种亲密浓厚的人类现实因其对某种神秘性的体现而具有天主显现 的(teofanico)价值 [5]。
本文建议读者“品尝”一种美食神学式的思考,以确认它在人类及属灵方面的丰富性。为此,我们邀请您踏上一段内心之旅,与上文提到的作者若瑟·托伦蒂诺·门东萨进行对话。为了引导读者通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智慧,他在著作中邀请读者通过重温准备餐食的时刻而倾听沉默的声音,观察无形的事物,触摸肉体内在及以外的事物:“烹饪能够唤醒一个或许是最亲密、最原始的部分,它构建我们,关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我们为求生而进行的斗争、我们的快乐与相遇,而在这一切之中,我们对事物带来的变化也是我们内心变化的反映”[6]。
托伦蒂诺认为,基督信仰对构建全球智慧、新的“人类语法”的贡献在于传播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灵修方式,特别是对塑造个体(通过身体感官)和社会(通过友情)的关注。因此,追随耶稣基督,基督宗教的人类属灵观绝不能被理解为与我们生存的物质性相对立。恰恰相反,它所面临的是脱离实际的危险和构建一种“非实体”在世方式的诱惑。因此,恢复与食粮关系的起始性非常重要,在食粮这一关系到生存的“场所”中,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独特的自由生活方式,在与世界、他人及天主的关系中实现自我转变。在本文中,我们将探索托伦蒂诺如何根据聚餐、烹饪和斋戒这三个轴心来理解这条打开人性的“美食神学”之路。
普遍挑战:通过聚餐而彼此接近
托伦蒂诺回顾了教宗方济各经常在三钟经结束时对听众所说的一句问候:“祝大家主日快乐,午餐愉快!”。这句问候虽然平凡,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其中所展现的是一种“看似平庸,但实际上却非常罕见的能力,它使你变得平易近人,表达你对他人实实在在的关心”[7]。正是因为提及进餐的事,这种平易近人的感觉才油然而生。在世界各历史时期和不同文明中,一起进餐–“餐桌共融”–所涉及的是一种建立关系的活动:用餐者易于“超越将自己与他人分隔开来的空间”,并“克服将生人与熟人分隔开来的障碍”[8]。无论是一起进餐,还是像兄弟般地祝愿他人愉快进餐,其关键在于缩短距离感,使不同人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虽然食粮对于每一种生物来说都属于需求范畴,但当我们开始“聚餐”时,就会发生一种象征性的变化,即:“将满足基本需求转变为影响深远的社交时刻”[9]。当一个群体一起用餐时,餐桌就变成了一面镜子:“餐桌上的与人为伴将对食粮的需求转化为一种微观世界,反映出充满意义的愿望与禁忌、实践与交流。通过对进餐方式的观察,我们可以窥见特定人类群体的内部结构、价值观、等级制度,以及该群体与周围世界所建立的界限”[10]。
事实上,无论是我们的个人经历还是人类饮食习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有关奠基、生辰、成人仪式、胜利以及哀悼、危机和困难等事宜的庆典”,都是围绕餐桌举行的[11]。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将餐桌仅仅视为体现约定俗成的文化规范、社会结构、等级制度及种种偏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场所,是个人及群体共同塑造人性的地方[12]。
在古代地中海社会,餐桌上分享的话语(或餐后遭受的背后议论)也可以向其他用餐者揭示个人身份。托伦蒂诺回顾了希腊文学中的一个名人事例:在《伊利亚特》中,英雄尤利西斯正是在餐桌上逐渐揭示了自己的身份[13]。这位枢机认为,这并不只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事例,而是所有人都有可能经历的一种体验,餐桌是“展示自我的最佳时刻,因为每位共餐者都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作为礼物”[14]。交谈通过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而展开,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他人的接纳:我们将这种深度欢迎称为“招待客人”。托伦蒂诺是这样解释的:“招待客人是一种语言契约。它是一个时空,在这个时空里,讲述通过对自身的讲述而完成。在聆听者面前,一种自传式的可能性被打开,将零碎的片段重新组合在一起,使断裂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发现轻声诉说生命内在结构的话语”[15]。
由于一起吃饭这一行为充满了浓郁的人性色彩,它成为各种宗教的核心范畴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基督宗教却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它有很多涉及食粮的方面,但却通过对食粮禁忌(吃什么、与谁一起吃、如何吃)的相对化而颠覆(sub contrario)对食物的禁忌”[16]。以保禄关于性与聚餐的反思为依据,托伦蒂诺请人们注意新生的基督宗教如何寻求一种新的实践并构建新的象征,从而提出一种取代古代社会合法化机制的社会方案。托伦蒂诺认为,为了解释并活出耶稣的好消息,“性和餐桌是基督宗教必须关注的日常生活组织的重要轴心”[17]。
归根结底,这一挑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餐桌是一种象征性界限,可以证明在差异之外进行共融的根本可能性”,那么这种接近可能会使我们感到恐惧。即使是诸如施舍的善意举动,也可能是“良知的最后避难所,以逃避在共融面前所感到的恐惧和不安”[18]。我们的人性不是通过馈赠物品,而是在对自我的表达中得以实现。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生活在孤独或无法沟通之中,这种负担也许在餐桌上更为沉重”[19]。由于共餐,生命的奥秘得以彰显:“无论是在倾听和交谈中,在沉默和欢笑中,还是在给予和关爱中,我们都是彼此之间一种必要的营养,我们的生命是由生命力来滋养的,而这一生命力是共同分享的”[20]。因此,在围桌而坐与他人聚餐之前,还必须关注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
个人的投身:揭开生活厨房的神秘面纱
聚餐是一个公共空间,是相互(能否)以客相待的体现。然而,餐桌并不是展现这种接纳的唯一场所。托伦蒂诺与某些其他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对用餐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与用餐之前发生的事情之间的某种二分法提出质疑。一方面,餐厅是“一个充满欢乐、秩序、规范和礼仪的地方,备餐工作无可挑剔且具有装饰性,就像一个戏剧场景”[21];这个空间被视为“喜乐的地方、放松的时刻、愉悦的间歇”[22]。另一方面,厨房则是“属于幕后技术人员”的场地,这个地方“更贴近现实,但也更不完美、不整洁,虽然到处都是飞溅的污渍和抹布,却不会有人在意”[23];这个空间往往被视为“既低贱、辛苦又往往不被重视的工作象征”[24]。
然而,如果生命是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么厨房便是一个本真的处所,一个从根本上接近构成我们个人和集体存在的空间。对于一位人类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厨房是生存本身的隐喻,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某种随着生存而改变自己的能力,这种流动性不仅是地域性的,而且是整体性的。在每一个厨房里都发生着如此众多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几乎对它们熟视无睹。厨房是具有不稳定性、探寻性和不确定性的地方,其中既有种种意想不到的混合物,又有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厨房经常处于无常状态的原因,因为它生活于潜在的重新组合中。厨房所凸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事物的改造反映着我们内心所发生的变化”[25]。
托伦蒂诺邀请我们关注这一往往由于偏见和恐惧而被人“视而不见”的场所和习俗。根据聚餐者在餐桌上讲述自己生活的方式,其中更深层的真相可能会被隐藏起来。事实上,在我们的叙述中,对日期、大事和非凡事件的关注往往无法解释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生活中最强烈的印记实际上是厨房范式所揭示的这种无声的、沉浸的维度”[26]。这种对隐藏在平凡中的事物的关注是米歇尔·德塞多(Michel de Certeau)所提出的历史学、人类学和灵修学方法的核心。托伦蒂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指出:“日常生活是我们从内心深处密切关注的东西。按照贝吉(Péguy)的说法,我们不应忘记这个‘记忆的世界’。这样一个我们内心深处的世界,是嗅觉、童年时生活的地方和身体的记忆,是对童年时的举动和快乐的回忆。[…]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日常生活是无形的”[27]。
文化人类学和神话也有助于对我们与烹饪之间的象征性关系的认识。托伦蒂诺重温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关于南美热带森林土著神话的著名研究《生食和熟食》(Le cru et le cuit)。他对其中关于烹饪中使用火的描述尤为关注。他回顾说,根据这位法国人类学家的观点,“烹饪标志着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生食代表事物的自然状态,而熟食则反映了由人操作的转变”[28]。因此,厨房代表着人性化现象的发生地,而这种人性化则被理解为与自然的区分,与自然环境拉开距离或取得自主[29]。
与普罗米修斯神话奇特的相似之处在于,大多数南美土著神话都将火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关的烹饪–视为与神性现实的分离。即使并未提出这一范畴,烹饪与神的分离也同样被理解为某种人类中心主义:它总是“集中于人及其可能性”[30]。托伦蒂诺认为,烹饪的出现代表了这些民族的一个身份认同的契机:“通过对烹饪艺术的拥有,人类宣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31]。这种属灵性和象征性的冲突真的与我们的当代问题相去甚远吗?
以厨房的比喻来谈论人类的存在,也就是承认我们的独创性在于能够在转变中生活[32]。托伦蒂诺对属灵生活提出了质疑,他赞同圣女大德肋撒对那些出于服从而投身于实际工作的修女的看法:“现在,她们在属灵生活方面的进步显得如此之大,令我惊讶不已。所以,来吧,我的女儿们,振作起来!当顺从要求你们不得不处理物质方面的事务时,比如做饭,想想主也行走于锅碗瓢盆之间,彻内彻外地帮助你们”[33]。
这一观点是人类自我认识和理解天主奥秘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天主也行走于锅碗瓢盆之间”这句话中,大德肋撒引导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自由与天主的自由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如果天主临在于人们的厨房中,那就意味着“祂并不责怪人类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自然和造物的空间。祂以激励者的身份出现”[34]。因此,与厨房中的这位天主建立真正关系的问题不再是分离,而是相反:“这是一个如此亲密的近距离,甚至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35]。
在与天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补充说,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有两个重大选择:一是选择接近和现实,正如大德肋撒的轶事所暗示的那样;二是选择距离和表象[36]。在第二种选择中,与天主的真正冲突在于以装饰之名而放弃将天主融入具体生活中。在这方面,托伦蒂诺提到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著作Miti d’oggi(《今日神话》)中所提出的批评。他在回顾巴特对《Elle》杂志所推出的烹饪“装饰性”料理的分析时表示:“装饰遵循两条相互矛盾的路线:一面以一种狂热的巴洛克风格逃离自然[…],一面试图以一种畸形的矫饰重建自然”[37]。
托伦蒂诺对我们灵性生活所面临的这种威胁发出了警告,并重申厨房是防止这种偏移的有效补救措施:“也存在一种完全流于形式的灵性生活,向我们推出诸如在柠檬片上插樱桃以及疯狂装饰我们内心旅程的季节性建议。我们的灵修生活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装饰性呢?解决方案或许在于回到我们的厨房,意识到天主真的临在,让我们在自身最深刻、最真实的部分重新发现友谊和愿望的经纬”[38]。
用美食神学的语言来说,那些谈论愿望的人实际上是在谈论饥饿。这种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感觉是否可以带给我们某些感悟呢?
一个矛盾性选择:通过禁食充饥
如果不对饥饿和禁食进行反思,那么这一关于食粮的启蒙之旅将是不完整的。禁食意味着自由地踏上节制之路,即“少的选择,减少生活所需,以求从中获取最大的意义”[39]。也就是定期或长期地遵循一条与充沛相反的道路,充沛可能导致合并,将所有一切全部混杂在一起,包括“适宜的和多余的;独特的和重复的;原创的和平庸的;消费的可能和幸福的承诺”[40]。因此,托伦蒂诺将所有形式的禁戒–禁食、禁消费以至禁批评–全部视为一种能够“拓宽我们的自由领域” 的灵性活动[41]。
托伦蒂诺认为,这种精神行为卓有成效:禁食“赋予新的可支配性,可以使更好的辨别成为可能,甚至可以促进我们的幽默感,使我们与最贫穷的人休戚与共”[42]。禁食所测量的内心旅程必须使我们远离“掠夺性做法”,超越“对个人利益的一味追求”,唤起“关系的一种新质量、新风格” [43]。如果人类的生存始终处于转变之中,那么这也会影响我们与世界结构的关系,因为这一结构 “鼓励对地球资源的贪婪攫取”[44],从而导致他人被迫遭受饥饿的丑闻。
禁食因此而兼具道德及生态意义,它意味着主动节制进食愿望的选择。为了说明这一点,托伦蒂诺例举了一个十分美丽却又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那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沦为一个集中营囚犯的意大利诗人托尼诺·格拉(Tonino Guerra)的诗作《蝴蝶》(La farfalla):“满足,真正的心满意足/生命中,我曾经历过多少次/但从未像/在德国重获自由的那一刻/我凝视着一只蝴蝶/却没有吞吃它的欲望”[45]。
除了扩展我们的自由、增强与穷人和世界休戚与共的意识之外,托伦蒂诺还邀请我们深入禁食这一古老习俗的核心。在他看来,“禁食的关键在于使我们对自己提出更深层次问题的可能:从我们得到的营养,到我们生活中梦游般的贪婪”[46] 。正是在节制中,在禁食所比较出的匮乏中,我们既能意识到自己与世界和他人之间的捕食关系,又能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使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与共食和烹饪一样,禁食也是一种有益于“皈依实习”的体验[47]。
托伦蒂诺所说的是怎样的一种皈依?他提醒我们,《圣经》中有关禁食的概念并未将其视为“由于我们沉浸于暴食而进行的一种纯粹的排毒”,而是“作为一种同时具有象征性和真实性的手段,以表达我们真正的生活食粮是别的,是在别处”[48]。托伦蒂诺在谈到这种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望的真正食粮时,引用了葡萄牙道明会修士、文学和符号学教授若泽·奥古斯托·莫朗(José Augusto Mourão)的如下观点:“我们内心所渴望的,与其说是我们似乎感觉需要的物品,不如说是我们生活的一切的基础:生命礼物”[49]。卡洛斯·玛丽亚·安图内斯(Carlos Maria Antunes)隐修士也在其《Só o pobre se faz Pão》一书中对此予以肯定:“斋戒使我们变得脆弱,让我们直面赤裸的自身,摆脱种种面具的束缚,从而认识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赤贫。它向我们揭示,我们的饥渴不仅是因为面包,我们最深切的渴求永远是对另一位的渴望。通过拓宽我们的心田,这种渴求会转变为一种独特的接纳形式,让我们在各自的本色和最纯粹的真实中接纳自我和他人”[50]。
在人生旅途中,为不足留出空间意味着做出一个根本性的决定:“轻装的旅行者是那些事先决定携带必需品,总是在行装中留出空间的人”[51]。我们的个人转变在与他人前所未有的自由相遇中实现,生命只有在自由开创出的空间中才能继续发展。
* * *
这种对人类状况的美食神学解读揭示了自我转变过程中所蕴藏的智慧,而这种转变过程是自由开放的,是每个人的生活,与厨房、聚餐以及对近人饥渴的感知度紧密相关。事实证明,回归日常生活、培养兄弟情谊是两种美好的途径,可以引导我们面对自身特有的人性,与我们的现实生活重建神圣盟约。为了活出这一切,信友们可以依靠上主的帮助,那位“懂得如何耐心重建盟约”的上主[52]。
事实上,耶稣所参加的聚餐不胜枚举,而且寓意深刻:“餐桌和聚餐已成为基督宗教记忆、相遇和乌托邦的最佳场所”[53]。托伦蒂诺认为,这些聚餐必须被理解为“表演行为”,是耶稣伟大计划的实践:“《福音书》有多处关于聚餐的描述,如果我们基于奇迹和美妙的视角来阅读,那么这些聚餐的意义就会被削减,这种视角虽能引起我们注意,却不会让我们担忧,因为我们会轻而易举地从奇迹中到满足,而忘记了聚餐是耶稣的演示行为,祂通过这些行为明确了祂的计划中令人不安的一面,即把那些通常无法聚集在一起的人召集在同一张桌子旁,在一个兄弟般的平等空间里接纳众多的男男女女”[54]。
耶稣是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希望并能够引领我们到达天主奥秘与人类奥秘相遇并建立盟约的地方:在那里,生命在爱的自由中成为他人的食粮。
- J. Tolentino Mendonça, Le temps et la promesse. Pour une spiritualité de l’instant présent,Nouan-le-Fuzelier,Béatitudes,2016,30(意文版:La mistica dell’istante. Tempo e promessa,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15)。 ↑
- 为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见 F. S. Adão, «A teogastronomia: uma estética teológica sui generis», in Perspectiva Teológica 54 (2022/3) 585。(葡萄牙语版和英语版)可参见www.faje.edu.br/periodicos/index.php/perspectiva/article/view/5131。 ↑
- C.A.Dória, Estrelas no céu da boca.Escritos sobre culinária e gastronomia, São Paulo, Senac, 20102 , 16 s. ↑
- 社会科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近一个世纪,因为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可以被视为“总体社会事实”。例如,参见 M. Mauss, Essai sur le don, Paris, PUF, 2012; C. Lévi-Strauss, Le cru et le cuit, Paris, Plon, 1964(意文版:Il crudo e il cotto, Milano, il Saggiatore, 1966)。此外,在当代神学思考中引入烹饪视角并不罕见,例如以下作品:S. Bonnet, La cuisine d’Emmaüs, Paris, Cerf, 1979; G. C. Pagazzi – F. Manzi, Le regard du Fils. Chris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Namur, Lessius, 2006; A. Méndez Montoya, The Theology of Food. Eating and the Eucharist,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9; G. C. Pagazzi, La cucina del Risorto. Gesù «cuoco» per l’umanità affamata, Bologna, EMI, 2014. ↑
- F. S. Adão, La vie comme nourriture.Pour un discernement eucharistique de l’humain fragmenté, Paris, Éditions Jésuites, 2023 (forthcoming 29 June 2023). ↑
- J. Tolentino Mendonça,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Paris, Salvator, 2014, 93. ↑
- Id., Le temps et la promesse…, cit., 101. ↑
- 同上,第102页。 ↑
- Id.,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102. ↑
- 同上。在就这一主题与意大利饮食传统史学家马西莫·蒙塔纳里(Massimo Montanari)的反思进行对话时,托伦蒂诺将膳食描述为“一个极具传递信息效力的参照物,我们不妨试想膳食具有镜子的潜能:其中汇聚着一种文化中最内在的一些规则”(J. Tolentino Mendonça, A leitura infinita. Bíblia e interpretação, Lisboa, Assírio & Alvim, 2008, 160)。Bíblia e interpretação, Lisboa, Assírio & Alvim, 2008, 160)。参见M. Montanari, «Sistemi alimentari e modelli di civiltà», in J.-L. Flandrin – M. Montanari, Storia dell’alimentazione, Roma – Bari, Laterza, 1997. ↑
- J. Tolentino Mendonça, O hipopótamo de Deus.Quando as perguntas que trazemos valem mais do que as respostas provisórias que encontramos, Lisboa, Paulinas, 20133 , 23. ↑
- 参见 Id., A leitura infinita…, cit., 160。 ↑
- 参见同上,第162页。 ↑
- 同上,O hipopótamo de Deus…, cit., 24. ↑
- 同上,A leitura infinita…, cit., 162。另见同上,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103. ↑
- 同上,O hipopótamo de Deus…, cit., 27. ↑
- 同上,A leitura infinita…, cit., 131。保禄的思考参见致格林多人前书:参见格前 6:12-20。 ↑
- Id., A leitura infinita…, cit., 156. ↑
- 同上,第160页。 ↑
- 同上,O hipopótamo de Deus…, cit., 25 ; 另参见:同上,Notre Père qui es sur la terre, Montréal – Paris, Novalis – Cerf, 2013, 111. ↑
- 同上,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88 f. ↑
- 同上,89。 ↑
- 同上,88 s. ↑
- 同上。 ↑
- 同上,A leitura infinita…, cit., 159; 另参见:同上,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1. ↑
- 同上,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2. ↑
- M.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 Arts de faire, Paris, Gallimard, 1990. Cfr J. Tolentino Mendonça,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3. ↑
- 同上,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0。参见Lévi-Strauss, Le cru et le cuit, cit.。 ↑
- 参见 J. Tolentino Mendonça,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0。 ↑
- 同上,第91页。 ↑
- 同上,A leitura infinita…, cit., 146. ↑
- 参见 Id.,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1。 ↑
- 同上,第86页。圣女大德肋撒的这句话出自Livre des Fondations de Thérèse de Jésus, cap. V, 7-8。 ↑
- J. Tolentino Mendonça,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1. ↑
- 同上,第87页。 ↑
- 参见同上,87; 89 s. ↑
- R. Barthes, Miti d’oggi, Torino, Einaudi。另见:J. Tolentino Mendonça,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8 s. ↑
- J. Tolentino Mendonça, 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9. ↑
- 同上,Le temps et la promesse…, cit., 105. ↑
- 同上。 ↑
- 同上,Notre Père qui es sur la terre, cit., 107. ↑
- 同上,第107页。 ↑
- 同上,Le temps et la promesse…, cit., 104. ↑
- 同上,第103页。 ↑
- T.Guerra, O mel, Lisboa, Assírio & Alvim, 2004。另见:J. Tolentino Mendonça, Le temps et la promesse…, cit., 84。 ↑
- 同上,第102页。 ↑
- 同上,第103页。 ↑
- 同上。 ↑
- 同上,102 s。参见 J. A. Mourão, Quem vigia o vento não semeia, Lisboa, Pedra Angular, 2011。 ↑
- J. Tolentino Mendonça, Le temps et la promesse…, cit., 104。参见:C. M. Antunes, Só o pobre se faz Pão, Lisboa, Paulinas, 2011 (意文版:Solo il povero sa farsi pane, Milano, Paoline, 2014). ↑
- J. Tolentino Mendonça, Le temps et la promesse…, cit., 106. ↑
- 同上,Notre Père qui es sur la terre, cit., 21. ↑
- 同上,Petit traité de l’amitié, cit., 94 s. ↑
- 同上,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