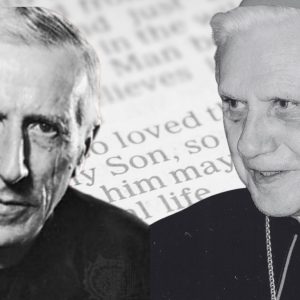在我年轻时,有一次,当我和家人一起在一个超市里的时候,一位非常热心的女士走近我的父母,对他们失明的可怜儿子表示同情,并询问说:“他每天都做什么?”。 “从事法律工作”,我回答道。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教会中也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即某些人不愿承认残障人士所应有的与其他人一样同为天主子女的生活:他们与其他所有人一道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努力工作,给与许多贡献及才智。一种普遍的歧视仍然存在于教会中。出入建筑物往往存在着障碍,文件不会以所需格式提供,而且往往基于不能反映残障人实际生活的假设。比如说,当我申请加入耶稣会时,我最初得到的回答是最好选择一个“学术性”较低的修会。只有在告知圣召负责人我正在完成博士学位的情况后,我才被接纳(我在当年之内便读完了学位)。实际上,残障人士得到网络和团体的支持并作出自身的贡献。我们同样是教会成员[1] 。
非常荣幸的是,我不仅生活在一个堂区内,而且属于一个休戚与共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同时,无论是在加入修会生活之前还是现在,我都得到了自己家庭、朋友和团体的支持,他们不仅满足我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带给我信仰上的陪伴和走向成熟以及明智的建议。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我努力与其他人合作,为遭受痛苦的人争取一个更好、更公平的世界,这些人往往处于教会和社会的边缘。
然而,根据我的经验,许多残障人士被允许融入社会的程度更为有限。一些人受到完全的排斥,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勉强接受允许的和制度化的参与方式。教会中确实存在某些具有针对性的团体参与形式(例如方舟[L’ Arche]、信与光[Fede e Luce]以及各种针对聋人的堂区团体),但这些团体往往由于仅由残障人士组成而缺乏开放程度,难以取得与整个教会互动的机会以及参与更广泛教会对话的可能性。
特别是正值我们准备召开世界主教会议之时,教会更应接受并切实履行教宗方济各在通谕《众位弟兄》(FT)中所作出的重大宣告。他在这部受到天主教残障人士极大欢迎的通谕中指出:“我想起在社会上被视为外方人的「隐蔽流亡者」。许多残障人士「在生活中没有归属感和参与感」,而且仍然有许多事物「妨碍他们充分行使公民权」。我们不仅要援助他们,也要让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公民社会和教会团体。这是一个艰巨和劳累的过程,但有助于逐渐培育良心,使我们能够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独特和不可重复的人」”(FT98)。
这种接纳必须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考虑。关于前者,事实上,我们的神学至今仍受到两种不同理念的侵蚀:一方面是那种将残障人士置于原罪持久重压之下的理念;另一方面是那种将其视为“可怜的受害者”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人子的特殊偶像”的理念。两者都既没有为恩宠甚至也没有为洗礼留下空间。倘若洗礼不能涤除罪恶或赋予恩宠,那么它究竟意义何在?
然而,我们既非偶像也不是生命的提醒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残障对神学百无一用。它可以提醒我们人性的局限性。诚然:我们这些残障人士缺乏其他人所具备的能力,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所有人都有局限性。我们与生具有的能力便是相当有限的。即使它们随着我们的成熟而增长,但同时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局限性和弱点是人生条件的组成元素。问题的浮现是由于社会只注目于某些方面的无能,而对其他无能则毫无察觉。在老人院和幼儿园里找到无障碍坡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图书馆、市政大楼、教堂和法院等建筑物外部,这种情况却并不常见。正是这种“不可进入性”使伤残(如失明或瘫痪)变为残废(无法重新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发挥我们的作用)。
这些对人类能力的限制意味着救赎是一项团体工作。我们彼此依赖,也依赖天主。我们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但这并不是亵渎性的、自给自足的完美,使我们与自己的创造者平起平坐,而是有能力与祂和我们周围的人建立关系。我们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完全信任天主和我们的兄弟姐妹。正如圣保禄在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所言:“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如果脚说:「我既然不是手,便不属于身体」;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如果耳说:「我既然不是眼,便不属于身体」;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若全身是眼,那里有听觉?若全身是听觉,那里有嗅觉?但如今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个个都安排在身体上了。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那里还算身体呢?但如今肢体虽多,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比较欠尊贵的肢体,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我们不端雅的肢体,就越发显得端雅。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须装饰了。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对那缺欠的,赐以加倍的尊贵,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反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格前12:14-26)。
一个能够对这些事实做出肯定并将其体现于神学中的教会,将是一个像教宗方济各所说的使浪子回头的教会。然而,在日常实践环境里对于残障事实的处理中,教会面对一个独特的情况。我发现,团体生活尤其能滋养参与和圣事性共融的感觉。无论是分享一台弥撒、一段祷告还是一顿晚餐,我都从一路同行(syn hodos)的人那里得到了巨大的礼物。即使作为司铎,我也会与他人一同庆祝圣事,分享喜怒哀乐,进入幸福和希望的世界(在弥撒或洗礼中),并接近处于痛苦中的人(如陪伴临终者或在移民收留中心遭受暴力者)。此外,我的局限性也为自己的司铎工作提供宝贵的见解。等级制度的观念往往导致倾向于专制的圣职观点,以至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导致骄横无礼和职权滥用。作为一名残障司铎,我认识到自己以及我所服务的人所共有的人的局限性。因此,我能够不以职权而居高临下地对待别人,而是从普遍弱点的角度出发与他人共处。
虽然扶助残障人士的世界超越信仰和堂区的界限,但依然形成一个团体。我们一度生活于歧视和边缘化中,而现在则得到了相互支持的机会。在残障人士团体内,即使是在诸如家庭及堂区一类的传统支持体系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也都习惯于在局限性中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帮助。
我认为,教会使命必须涵盖这种相互支持,这并不意味着去告知人们具体情况,而是去关注残障人士的经历,并沿着教宗不断指明的道路,将最边缘化的人置于福传的中心。从本质上讲,我们同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所有人同样分享着基督所“取得”并将其“圣化”了的人性,尽管既脆弱又有限。
在政府对服务实行配给(往往明确以身体或精神能力为依据)的新冠时期,残障人士之间的互助为许多人提供了支持。自纳粹主义以来,某些人首次公开倡导优生学。在那段晦暗的时期,残障人士相互支持,提供信息和帮助。保禄给格林多人的信息这一生动体现,可以向堂区、教区以及教会领导者展示团体中培养和实践个人关怀(cura personalis)的正确途径及最佳组织方式。
这种转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扩展到教会生活和管理的每一个方面。残障人士可以平等地参与教会礼仪,并享受充分的权利。我们可以成为行政机构的成员,无论是在堂区和教区,还是在法院及教区公署。在决策协助下,即使智障人士也可以在影响其生活的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整个社会。
如果我们不属于一个给我们说话的教会,那么她的声音就不会得到妥当的传达。残障人士可以而且必须承担教会职务。残障神学家的声音正在逐渐出现。他们应该得到超越现有的支持和鼓励。我相信,圣神如今正在创造一个可喜的变革机会,而且教宗方济各已经抓住了这个机会。
每一个生命都包含着一个世界。因此,占比15%的残障人士带来了五彩缤纷的观点和故事,等待着我们去聆听。我们可以在教会中各个非残障人士工作的领域工作。此外,我们还可以为基于我们的残障的边缘化和歧视性认识提供切实贡献。我们可以使教会对其局限性和团结潜力有一个新的认识。正如教廷的平信徒、家庭和生活委员会所指出的,我们也是教会。因此,让我们携手同行:不再是“我们”和“他们”,或是流亡者和公民,而是在基督耶稣内合而为一。
- 参见J.Glyn,《“我们”,而不是“他们”:教会与残疾问题》,https://www.gjwm.org/2020/09/21/noi-non-loro-la-disabilita-nella-chie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