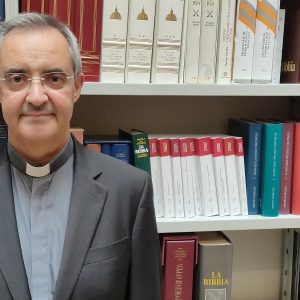许多人都对16至18世纪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有所耳闻,他们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利玛窦。利氏之被载入史册,是由于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主角;而于教会而言,也是因为他是以“本地化”形式向中国传教的典范。总体而言,“本地化”是指向在文化上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民族宣讲福音。然而,利玛窦仅仅是一位先驱,继其后还有无数其他杰出人物,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于科学技术(天文学、数学、水力学、铸炮……)、文化(翻译儒家经典作品……)、艺术(绘画、建筑……)等方面,以至于有人质疑耶稣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文化交流还是传播福音。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推动传教士的内在动力是宣讲福音以及福音启示下的基督徒生活的新意。本文将着重关注其传教活动中鲜为人知的一个方面及其所得到的回答: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中国妇女[1]。
初期中的洗礼、告解及加入团体生活
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女子必须对父母、丈夫和亲戚百依百顺,在其管制下度过极度封闭式的生活。因此,传教士与她们的直接联系实际上不仅不可能,而且反而需要回避,以免遭受拒绝和引起猜忌。更重要的是,耶稣会士们很快便放弃僧侣穿戴及其生活方式,以士人生活方式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民间女子可与僧人有所交往,但出身于高门的女子却倍受严格的社会管制[2]。
经过多次努力,罗明坚(Ruggieri)和利玛窦(Ricci)神父得以在南方肇庆建立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第一个住所并在那里居住了六年。此间,从他们那里领洗的人数总共不过七、八十人(不包括受洗的夭折儿童),但在最后一年,即1589年,“最后一次领洗的人数总共十八个,其中包括一些受敬重的年长妇人,她们在家庭中寄予基督信仰以极大信任和支持”(FR I, 261)[3]。这便是第一批加入教会的中国妇女!当然,她们身为士子的夫人或母亲,而这些士子则均属已经领洗亦或与两位传教士交往甚密的人。两位传教士无法以任何直接方式而只能通过第三方向她们传教(同上,第2页)。后来,在别处,这也成为接近妇女并使其能够受洗的惯常方式。
1600年,在南京,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神父得以为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授洗,其中首先是一位有权威的长者,取圣名为保禄,“随后入教的是他的小儿子马蒂诺以及他的几个侄子,这全家男女老少及其亲属是南京最早也是最优秀的基督徒”(FR II, 93 f)。后来,马蒂诺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身居要职,并于1604年在北京中举。此外,在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妇女经罗儒望神父(p. João da Rocha)授洗奉教(FR II, 254, no. 6)。
1601年似乎是一个转折点, 由活跃于韶州的龙华民神父(p. Nicolò Longobardo)推动而促成。此前,鉴于当时妇女足不出户的情况,传教士们已不再讨论对她们授洗的问题,反倒是新入教者自己坚持要给他们的妻子授洗。因此,龙华民致函利玛窦及其他神父,并征得他们的一致赞同。“经验本身最终证明,吾主并未排除她们与祂相识的机遇。恰恰相反,她们带来的成果如此显著,以至其中不少人甚至比男子做得还要出色”(FR II, 203)。
一段精彩的文字这样描述了一位决定领洗的官吏的经历:“他的母亲和祖母在他之前领了洗,而他本人那时已然处于望教和慕道期间。在聆听教义之后,他就会前往她们那里照样再讲给两位长辈;就这样,他们慢慢地完成了很好的慕道学习。两位女子在圣亚纳庆日领了洗,她们的两个儿子也都在场。神父对她们进行了必要的指导和提问,发现她们接受了很好的慕道准备。那位母亲取圣名玛丽亚,祖母取圣名亚纳”(FR II, 204 f)。这个故事继续叙述了那位官吏的领洗礼以及这些妇女的信仰热忱和榜样。应该指出的是,她们也喜欢与成为基督徒的其他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以至农家女子聚会,并且待她们“亲如姐妹”,那些场景宛若“奇迹”。
1601年的“年度信函” –即耶稣会士写给罗马的报告–讲述了对妇女施洗的过程。在一个家庭成员吩咐完毕之后,“即在他们家里的一个大堂内立起一个祭坛,上面供有救主画像,并设有蜡烛和奉香。众位亲朋好友会蜂拥而至,随后到来的是传教士。传教士会在她们的丈夫和亲戚面前向这些妇女提出关于基督信理的问题–她们必须从头到尾熟记所有的教义–并询问基督信仰的主要奥秘。这些妇女在她们居住的内室中回答问题,并不因在外国人面前露面并接受询问这一中国女性世界的新景观而大惊小怪。洗礼仪式在 考问结束后举行;其后,神父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每个新教友赠送一顶头冠、一个十字架(veronica,耶稣的真实相貌)和一副圣像”(FR II, 204, no.4)。
另一个有关洗礼的趣闻发生在南昌,当时在那里传教的是李玛诺神父(p. Emanuel Diaz Senior)。1604年底,一位皇家宗室以若瑟为圣名接受了洗礼。紧接着,他的三个近亲也在主显节以东方三贤士的名字为圣名接受了洗礼。此后,年迈的母亲也想放弃她一度笃信的异教而接受慕道。对此,利玛窦神父叙述道:“我们的人安排在她家里进行慕道。另外,由于在中国大家闺秀足不出户,她并不必外出,而只是隔着一扇门帘在屋里听道,并在不露面的情况下作答”。在她受洗的当天,一个惊喜出现了!随同这位老妇人的还有另外一些妇女,她们在不抛头露面的情况下一起听完了整个慕道课程!“六个慕道者出来了,她们和她一起听到了所有的讲道。对于向其提出的问题,她们也都很好地一一作答。于是,她们一同接受了敷油及其他所有洗礼仪式,众人亦为此欢欣备至。随后,他们还在一个准备好的精美小堂里举行了弥撒”(FR II, 338)。德礼贤神父)(P.D’Elia)指出,利玛窦坚持进行所有的浸洗礼(“敷油”),“以彰显基督信仰取胜于中国古代妇女过度的封闭”(同上,第8页)。事实上,传教士们被迫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与妇女进行身体接触的巨大阻力:无论是浸洗礼,还是“终傅圣事”(在这种情况下,照常规亦需进行脚上傅油,但这无疑将引起极度不安,耶稣会士们遂未予以落实)。
此外,个人告解悔罪的做法也逐渐传播开来,并通过皈依的丈夫传向妇女。我们从利玛窦那里得到了第一个确凿证据–至少是在身为贵门女子的情况下–他所谈及的是一位1602年于北京领洗的士子,在接受关于七件圣事的教导之后,“他希望立即领受告解圣事,且以不同寻常的精神作了告解,一边为自己的罪孽黯然泪下。有了他的榜样,许多其他人也开始领受告解圣事,特别是他的儿子和其他家人,以至他的妻子:这似乎非常难办,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妇女足不出户,而这位基督善徒却为这项神圣的工作开辟了道路”(FR II, 309 f)。大约在同一时期,龙华民神父(p. Longobardo) 也开始在韶州为妇女举行告解圣事(参见FR II, 326)。一个女人不仅在与一个男子单独交谈,而且这个男子甚至是一个洋人,这的确可谓前所未闻的胆大妄为。即便是后来,为了施行告解,神父们也会被引入一个用帘子隔开的房间,在根本无法看到对方的情况下与女子交谈,同时,在房间另一处——听不到告解谈话的地方——总会有一个在场的第三者。
不过,也有一些情况和处所,尽管需要适当的谨慎,但与妇女的传教关系可以在不甚苛刻的限制形式下进行。相对于城市而言,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于乡村及大众阶层,特别是在中国北方。费奇规神父(p. Caspar Ferreira)的一段生动描述暗示了这一点。1607年,他访问了北京周边的一些村庄,而在此两年之前,庞迪我神父(p. Diego Pantoja)业已前往那里广传福音[4]。因此,费奇规写道,当他走近其中一个村庄时,“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小孩子如此欢天喜地地出来迎接我们,就好像他们都已是基督徒”。他被招待于一个大席棚下,“以满足那些希望听他讲道的人”。“在这里,来见我们的人各式各样,甚至有一群妇女,随同一位被尊为首领的女子,她们在其率领下一同聆听讲道及教义讲解,并在救世主的画像前焚烧经其负责收集的偶像。这位女子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热忱和投入”。费奇规继续写道,在村里逗留期间,“我向年长及已婚妇女传授教义和祷文,而我的弟兄负责男子,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孩子负责未婚女子”。在其他信息中,费奇规谈到一位年轻的女基督徒:入京探访狱中丈夫的她得到一位熟人的招待,此间,那家人每晚都在神像前一起祷告。这位年轻女子解释说自己不应加入这种崇拜,但她坚定不移地大谈其基督信仰,“以至有九家人要来听我们讲道并接受洗礼”。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批评。例如:“有些人指责说,与我们会面既已触犯中国习俗,勿谈与妇女交谈,以及为她们施洗时为其涂面(暗指傅油);然而,无论是通过这些诽谤,还是借着玩笑和威胁,他们都未能最终得逞”。费奇规神父还组织了一些善会,包括一个妇女善会。因此,上述堪称一个结构良好、团结一致的团体:“当我离开时,大家均前来送行,不分男女,就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一种旧日相识所固有的情谊”。总而言之,从传教初期伊始,向中国妇女传福音并使她们加入基督信仰团体生活的道路便已敞开,而她们本身也不失良机地表现出其热忱、奉献、使徒精神、主动性以至领导力。
明朝皇宫中的女性基督徒
在当时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在士人和政府官要中进行福传,而且要努力靠拢皇上,努力赢取龙恩以及允许基督信仰宣教的御准,甚至他本人的皈依。
利玛窦曾向皇帝呈献许多珍贵礼物,却未尝蒙召见。庞迪我神父是比利玛窦年轻的出色伙伴,他因教授一种为人所爱的乐器(即manicordio,一种羽管键琴)、为献给皇帝的钟表上弦并负责维修而得以进宫,从而对宫廷环境日渐熟悉。然而,在1618年“南京教难”之后,他被逐至澳门,必须重新建立联系。由此,于1623年进京的德国籍神父汤若望(p. Adam Schall von Bell)成为主角,他受朝廷重臣徐光启—被基督徒誉为 “保禄博士”—引荐,加入重要的“历法改革”计划,耶稣会士的科学、数学和天文技能在此计划中显示了其决定性作用。汤若望不仅是一位声誉日隆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一位有勇气的人,一位能干的使徒[5]。他开始探索将基督信仰带入皇宫的可行办法,那里的太监多达数千(据传闻甚至可达一万……),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大多被传教士们视为道德不佳以至贪腐者。
然而,宫中也有许多女子(据说约有2000人),其中有专门服侍皇帝、皇后及皇太后的女官及宫女,但不能将她们与内宫妃嫔相混淆。经过甄选,其中最出色的会被指派为皇帝的贴身宫女,她们与皇帝接近的程度远超过太监。巴托利(Bartoli)详细地解释了这些宫女的等级:“她们主要分为三个品级,第一品是最尊贵的女官,她们最贴近皇帝,掌管宫中大事;品级最高的女官有12人,她们能说会道,善文墨,通晓向皇帝呈报所用的官话”[6]。这些女官终日轮流侍候于皇帝寝宫之外,从太监那里接受需要处理的奏折,在读罢折子后向皇帝禀报其中的内容,并将经御批后的折子再送还太监。第二品宫女有40“她们负责照料皇帝的起居,主管服饰、文书、笔墨以及所有皇帝所触及或所要求的御用品”。第三品女官共30人,“她们为皇帝备膳、摆宴,侍候用膳,而且为其左右护驾;除此之外,她们还为皇帝清扫、整理寝室,掌管殿内的器物摆件”。 这头三等宫女是宫内仅次于妃嫔的人物,也享受太监和丫鬟的服侍。然后,还有侍候众妃嫔的宫女,她们所形成的是一个更庞大的第四品级。
除了宫里的太监,没有人可以和这些宫女搭讪。经过长期努力,汤若望神父终于在1635年结识了一位姓王的太监,时值明朝末位皇帝崇祯年间。王氏是一个罕见的德才兼备之士,他皈依了基督信仰,并以圣名若瑟受洗。基督信仰通过他在宫廷女官中得以传播。他按照汤若望的指教对这些女官进行慕道,直到最终为其施洗。1637年期间,基督徒女官已多达18位,包括三位圣名为亚加大(Agata)、海伦娜Elena)和依撒伯尔(Isabella)的一品女官,一位取圣名路济亚(Lucia)的二品女官,四位三品女官,八位四品女官,以及另外两位由于年长而出宫的前一品女官。很快,他们又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基督徒女官于1639年已经发展到40人,并于次年达到了50人!借助于王若瑟的周转,汤若望神父以书面形式对她们进行灵修指导;她们定期举行祈祷聚会;耶稣会会长任命其中的一位为该团体的“负责人”。不过,她们因为不能与外人接触而无法领受圣体。
汤若望的回忆录和耶稣会的其他史料记载了一些关于这个团体的奇闻趣事(诸如:虚荣心及炫目珠宝对她们的诱惑以及其他女官对她们的指正,蒙受冤屈以及对司御膳时打翻碗碟的恐惧,一位后来皈依的异教徒女官的嫉妒心理及其种种恶事,等等)[7]。诚然,这些并不掩饰其信仰的女官,彼此敬重、慈善谦卑, 她们的善德美行赢得了皇帝的赞赏。汤若望神父得以向皇帝呈献的一部精美基督生平画像和一尊珍贵的东方三贤士蜡像,这些圣像受到宫里人的敬拜,他希望皇上身边这些基督信仰的善表和基督徒生活氛围最终能使皇帝奉教……然而,一切均悲剧式地戛然而止。
1644年,明朝统治长期的衰落被推向极点。当满族人横扫中国北部并逼近京城时,北京落入起义军将领李自成手中。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自缢身亡,皇后及皇太子亦随之而去。经过短暂的平息,北京城在此间一片混乱,到处刀光剑影。满族人夺取了政权,创立了大清新皇朝。汤若望神父是唯一一个以巨大勇气留守京都的耶稣会士,他试图保卫基督信仰团体和接纳了许多难民的耶稣会馆。在那可怕的数周内,他特别关注保护妇女免遭暴力,说服她们不要像许多走投无路的人那样,为逃避强奸的耻辱而自尽。实际上,他的确成功地保护了数十名女子[8]。
宫女们在逃离皇宫的过程中被打散了。如果幸运的话,有些人能够重归家园,成婚生子,不过也有人会继续度处女生活。汤若望讲述了海伦娜(Elena)的例子:这位被公认为美丽绝伦的一品女官,被许配给一位满人为妾,在被带往新郎家的途中从桥上跳了下去。虽然被救,但摔断了一条腿,却也重获自由。此后,她与汤若望神父保持着灵修联系,并向他讲述了皇宫内的往事以及皇帝本人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
高瞻远瞩的汤若望留在了北京,并借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迅速得到了满人的青睐,尤其是摄政王及年少新皇帝的喜爱。因此,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期,他为天主教传教士赢得了一如既往的皇帝恩宠,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与此同时,其他耶稣会士–特别是毕方济(Sambiasi)、瞿纱微(Koffler)、卜弥格(Boym)等神父—则继续与坚守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南明分派保持密切联系。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在一位身居要职的基督徒太监的协助下选择奉教的宫廷妇女,只是,事情的结局在这里也同样糟糕。1648年,在明朝最后一位被推上皇位的永历“皇帝”的后宫(宫廷?)里,五位最尊贵的皇家女子接受了洗礼,其中包括永历帝的皇后亚纳(Anna)及皇太后海伦娜(Elena)。在她们受洗的几天后,永历的一个太子诞生了,瞿纱微神父在其父答应太子日后受基督信仰教育后同意为他施洗,即使永历帝对此并非心悦诚服。此太子得圣名康斯坦丁(Costantino),以示对一位未来基督徒皇帝的祝福!1650年,皇后海伦娜(Elena)分别向教宗英诺森十世及耶稣会总会长致函,肯求为保护大明王朝祈祷,并援助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这两封信函被委托于卜弥格神父,请他带往罗马转交。这些信件在历尽周折后终于被送到,而教宗那封写在黄色丝绸上的回信,却仍被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于梵蒂冈档案中:这封来自罗马的回信始终未能到达目的地。最后,在1662年,当满族人将其领地扩展到整个中国大地并从此而结束了长期战争之时,永历帝及族中男子被杀戮殆尽,康斯坦丁也不知去向。众后妃及其侍女则被押往北京,被终生关入一所陋宅,不可与外人接触。据耶稣会士方面声称,真正的信德及真诚的慈悲为她们这种漫长的囚徒生活带来了慰籍[9]。
钦封“淑女”甘弟大
然而,即便明朝宫女的沧桑最终并未能为人生增辉添彩,但一些杰出的女性人物却出现于基督徒团体之中。尽管不乏外部的压力以及动荡的环境,以至传教士之间的内部张力,但在有利的家庭和社会条件下,她们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并处于蓬勃发展中的教会的真正柱石[10]。其中最著名的无疑非甘弟大莫属,其名声甚至通过她的一位“灵修导师”传至欧洲。这位神父便是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他是以中国传教工作检察官的身份于1681年被派往罗马,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甘弟大一生的好书。这本书至今仍是关于我们的女英雄的主要资料,也赋予本文以创作灵感[11]。
甘弟大是雅各伯四男四女总共八个孩子中的一个。雅各伯是徐光启的独生子,徐光启于1603年成为基督徒,并成为利玛窦神父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弟子及好友[12]。虽然祖父担心断后,但出于对天主安排的信赖,他接受了基督信仰的规定——除了正房不得纳妾[13],并带领全家人接受基督信仰,而且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建立起上海的基督信仰团体。他始终是侄女的信仰、知识和道德灯塔。
甘弟大于1607年出生在上海附近的松江。之所以择此为其圣名,是因为在她领洗的那一天,瞻礼单上所纪念的殉道者是一位名叫甘弟大的圣徒[14]。关于其青年时期并无详实记载,无非是谈及她极为善良虔诚的为人而已:这对于一个虔诚的皈依者家庭可谓自然而然的事情。她在14岁时丧母,16岁时嫁与一位富有显赫的外教人。出于为传播基督信仰提供帮助的期望,年轻的基督徒当时可以与异教徒联姻,条件是新娘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她的婚礼上,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甘弟大与其家人实际上一起被免除了“敬拜”传统“偶像”的规定,而是在没有司铎在场的情况下于救世主画像前进行了瞻礼。在随后的14年中,甘弟大为她的丈夫生育了8个孩子。最终,她丈夫也在临终前皈依了基督信仰。甘弟大在30岁时开始守寡。
据柏应理所言,这于是成为一个改弦易张的转折点。这位早先已多次指出中国妇女不拥有丝毫自由的耶稣会士毫不含糊地表示,“在婚姻方面,守寡于中国妇女而言是一种自由的状态”。 对甘弟大来说,第二次婚姻完全不在她的考虑之中,因为“丈夫辞世之后,她已成为可以自己做主的自由人,其唯一希望是作天主子民”(HD 14s)。在这种新处境中,甘弟大以非常活跃的方式度过了另一段长达40年的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位负责任的母亲,甘弟大将继续照料自己的子女,其中尤其是巴西略:这个孩子虽使她煞费心机,但后来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并且始终对她感情很深。此外,她继续妥善管理人口众多的家庭;但由于不再处于一种隶属的状态,她在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并为促进基督信仰团体的生存和发展而与传教士开展紧密合作。在柏应理神父所叙述的无数善行美德中,本文只能在此回顾其中的寥寥几个。
作为名门闺秀,依照中国当时的习俗,甘弟大也是一位刺绣高手。她与自己的众位姐妹、女儿和女佣一起以绣活积攒了不少收入,“根据福音的劝导,她暗中将这些钱用以援助传教士、穷困者、建造大小教堂以及作为新基督徒的慈善事业之一切所需”(HD 24)。 为了这些工作,甘弟大并未挪用理应成为其子女遗产的家庭资产,而只是使用了她的个人劳动成果,她深信自己可以问心无愧地将这些成果自由地投入于慈善事业,并为此而引以为荣。
在1647年至1665年的20年间,得到甘弟大精神层面的合作及具体支持最多的莫过于巴勒莫(Palermo)人潘国光神父(p. Francesco Brancati),他是上海及周边地区基督信仰团体中的一位伟大使徒。甘弟大这样做乃是步其家父芳踪,他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基督徒。在这个地区,潘国光神父建起了多达90座的教堂以及45个祈祷所。甘弟大在捐献和礼仪用品等方面给予合作。此外,潘国光还组织了不同类型的“第三会(Congregazioni)”,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其一是“受难会”,于每周五进行关于慈善和悔过的操练,男子在教堂聚会时,而妇女则在家里做热心神工;其二是“圣依纳爵会”,为知书达理的男子能够在礼拜日到传教士无法前往的教堂讲道做准备;其三是“圣方济各会”,由教理讲授员向儿童传授教理。甘弟大“好比这些第三会的母亲”,向其提供由她自己出资印刷的书籍和画像,以及奖品、礼物和有助于各第三会生活及活动的各项所需(HD 37)。
甘弟大对妇女福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其祖父徐光启曾经鼓励和劝服利玛窦及早期耶稣会士翻译并出版有关西方科学文化的书籍,以协助他们进入中国儒士阶层;甘弟大也向传教士明确表示,为了让无法涉足教堂的妇女入教,他们必须用中文编写信仰类书籍。耶稣会士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柏应理提及耶稣会士到那时为止出版了126部信仰类和宗教类作品–而甘弟大则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分发工作,并将它们赠与所有她能接触到的妇女。此外,她坚决主张应该设立一个专门为妇女服务的教堂,以便她们在指定的时间内一同前往,参加除神父及辅祭以外无任何其他男子在场的弥撒圣祭;此外,神父还可以在那里讲道,尽管需要他们面向祭坛而背向在场的妇女。
由于婴儿死亡率极高,甘弟大致力于教授基督徒助产士如何为濒临死亡危险的婴儿授洗。许多婴儿被无法抚养他们的父母遗弃,其中尤其是女婴。甘弟大说服她当时已是有钱有势的儿子巴西略,让他腾出一所大房子来安置这些为数众多的孩子。当然,她还必须找来许多乳娘给他们喂奶,然后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抚养和教育。对于那些未能成活的孩子,甘弟大还在专门安排的一个墓地给与他们有尊严的安葬,并在墓地上题写了:Charitas omnia sustinet(“慈善关护每一个人”)的字样。在这些令人敬慕的慈善事业中,许多非基督徒以自己的奉献与以合作。
甘弟大的使徒创造力是独一无二的。她甚至与那些游荡于拥挤的街道上,以算命和“给人带来好运”为生的盲人打交道;她把他们聚集于一处,不仅向他们提供生活所需,而且还在信仰上给与指导,以至他们会诵念着“关于信仰的条文断句”返回街头,向“围观他们讲话的众人”传授“信理”(HD 76f)。
当柏应理神父受派前往欧洲时,甘弟大希望表达她对教会合一的深切感受以及对通过传教士而获得信仰的由衷感激。因此,她通过(柏应理)神父为罗马的耶稣会教堂送去珍贵的礼物,但最为重要的是,她协助收集了大量耶稣会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书籍并带给教宗,其中包括宗教和科学方面的文献共400多本,其中300多本经过核实,构成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第一批为数可观的中文书籍[15]。对教宗来说,了解中国教会的活力及信仰和文化的丰富性至关重要,以便继续通过祈祷和派遣新的传教士给予支持。中国教会有中文的弥撒书、礼仪书、日课经文及神学和神修教科书,因此,拥有本地神职人员并用中文举行礼仪已然是水到渠成之际。一位从传统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基督徒妇女,支援耶稣会传教士的修会代表(Procuratore),将这一信息、这些期望、这些要求带往罗马。
可能是由于其子巴西略的地位,这位伟大女性的善德名传北京宫廷。皇帝因此特赏甘弟大镶银锦袍一件、珠宝凤冠一顶,钦封她为“淑女”。虽然不喜财富,但出于对皇帝的敬重,甘弟大在寿日当天穿上了这不同一般的御赐锦袍、凤冠。无论是在柏应理神父所著甘弟大传略的扉页上,还是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6]中的一幅著名板画中,甘弟大均以衣着这套华丽服饰的形象出现。当然,这不是她的日常服饰,据说,她卖掉了许多珍贵的银饰,以充善款。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热衷于她的这一形象:这有力地证明,甘弟大的美德及其在慈善事业上的孜孜不倦不仅在基督信仰界,而且在中国社会为她赢得了敬仰。倘若说她的曾祖父保禄博士以实际行动表明,基督信仰可以激励人毕生献身于科学、知识、服务于国家,并立志肩负重任,那么她的孙女甘弟大则以切身表现说明,基督信仰可以激励一个中国妇女的承诺和责任,使她成为所有同胞的榜样,给他们以启示。
1680年10月24日,甘弟大在松江安息主怀,陪同她的有亲人及在上海附近传教的埃马努埃莱·洛雷菲斯(p. Emanuele Lorefice)神父,他们一起祈祷,神父为她施行了圣事。根据当时的习惯,她在银质十字架上铸下了她的信仰宣言:“我相信、我盼望、我爱慕三位一体的天主,赖耶稣的至圣之功,我坚信并热切盼望我的罪得蒙赦免,我的身体得蒙复活,以获享永生”( 这是根据意大利文翻译而来的中文白话文,碑文原文恕无以考证——译者按)。耶稣会总会长获悉后,命令在会每位神父遵照对修会最大恩人的惯例,为她献祭三台。柏应理神父在传记的结语中指出:“松江所有人皆视这位女子为圣人”(HD 146)[17]。我等亦然。
- 这篇文章的主要依据是当初那些耶稣会传教士之亲笔所作。为此,它们是来自“一方之见”的故事,应通过其他资料加以深化和补充。然而,我们所引用是可信的证词。 ↑
- 柏应理神父(P. Philippe Couplet)如此观察道:“的确,如果最先进入这个帝国传播福音的神父们继续以僧侣的穿戴出现,他们会更容易与妇女接触,因为她们可以自由地与这些崇拜偶像的僧侣交谈、前往他们的寺庙里祈祷;但这些早期传教士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判断:于宗教而言,与其和那些即使在没有探访及交谈的情况下也能通过阅读书籍或在其夫君指导下了解我们的奥秘的人打交道,不如与法官、儒生及当家人交涉更为重要”(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 Paris, Michallet, 1688, 8)。 ↑
- 我们将多次以《利氏史料集》(Fonti Ricciane,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为参考印证,此书在本文中的缩写为FR。这部史料集包括利玛窦所著《耶稣会及基督信仰传入中国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ristianità nella Cina),分三卷出版并附有德礼贤(Pasquale D’Elia)神父甚为可观的注释。 ↑
- 利玛窦在1607年10月18日致总会长阿夸维瓦(Acquaviva)神父的《年度报告》中转述了费奇规(Ferreira)的报告,参见M. Ricci, Lettere, a cura di F. D’Arelli, Macerata, Quodlibet, 2001, 447-451。 ↑
- 参考传记为:A. Vä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Köln, Bachem, 1933. ↑
- D. Bartoli, La Cina, IV, cap. 209. La famosa opera di Bartoli ha avuto molte edizioni: ad esempio, Torino, Marietti, 1825. ↑
- 关于这些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汤若望神父的回忆录手稿,题为Historia o Historica relatio (del 1660-61),其拉丁文本发表于H. Bernard (ed.), Lettres et Mémoires d’Adam Schall S.J., Tientsin, Hautes Études, 1942,附有耶稣会神父Paul Bornet的法文译本。关于宫中女子的逼真叙述请见第44-64页。另见A. Vä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cit., 122-124. ↑
- 汤若望是一个不同反响的人物。此前,他曾乔装成一个送炭人潜入基督徒将军孙元化的牢房,设法在他被处决前为其施行临终圣事。孙氏被判处死乃因其部队反叛之罪。在北京战乱期间,汤若望曾挥舞着一把吓人的日本刀把守门户,以震慑居心不良者… ↑
- 关于明末的这些事件,参见F. Bortone, I Gesuiti alla corte di Pechino (1601-1813), Roma, Desclée & C., 1969, 62-64 。此外,另一本书也谈到被囚禁于北京城的皇家女子令人同情的生活:Ph. Couplet, Histoire d’une dame…, cit., 105 s. ↑
- 卫匡国所记载的下述中国基督徒人数出自他的报告《Brevis relatio de numero et qualitate christianorum apus Sinas》(1654年):1627年,13000人;1636年,40000人;1640年,60-70000人;1651年,150000人。 ↑
- 据说柏应理起草了第一篇关于甘弟大生平的拉丁文手写原稿,但的确也出现了其他几种语言的印刷版本,其中首先是文中所提到的法文版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chinoise, Paris, Michallet, 1688(我们将在本文正文中引用该版本,并注明缩写HD及页码);随后是1691年在马德里以及1690和1694年在安特卫普(Anversa)问世的版本。耶稣会士C.G. Rosignoli也出版了一部意大利语版本,将甘弟大及其祖父的传记收录于同一卷中:Vite e virtù di D. Paolo Siu Colao della Cina e di D. Candida Hiu, Gran dama cinese, Milano, Malatesta, 1700。 ↑
- 关于保禄博士,请参见:费德里克•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徐光启 —— 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伟大的中国天主教徒》,链接https://www.gjwm.org/2021/08/23/xu-guangqi-un-grande-cinese-cattolico-al-servizio-del-suo-popolo-e-del-suo-paese/。 ↑
- 传教士们非常严格地要求一夫一妻制,并以拒绝纳妾作为领洗的条件。庞迪我神父相信,中国妇女会意识到这是对妇女尊严的坚决肯定,会使她们对基督信仰产生好感。他在其名著《七克》(克服七罪宗)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其中第三章的主题是色欲。 ↑
- 中国女子不同于男性,她们(有时可能——译者按)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是随父姓并在其后加上她本人的排行。然而,基督徒妇女却可以其圣名为荣,使她们感到自己在继承这些名字所纪念的殉道者及圣人的信仰。 ↑
- 参见C. Yu Dong, «Chinese language books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A Study on the Chinese missionary books brought by Philippe Couplet from China», in Miscellanea Bibliothecae Apostolicae Vaticanae, vol. VIII,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01, 507-554。从这些书目中不难看出为滋养信仰及宗教教育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其中的几本图书为潘国光神父所著,另有一本(罗Rho神父所著)被编为Centum selecta monita Sanctae Matris Theresiae(亚维拉的大德兰与圣依纳爵及圣方济·沙勿略同于1622年被封圣)。这或许是关注妇女灵性生活的一个具体标志? ↑
- J. B.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Paris, Le Mercier, 1735, 4 voll. ↑
- 我们未能获得任何有关甘地大墓葬的最新可靠信息。然而,据徐Censien神父(圣名西满,徐氏后裔)报道,似乎在1937年3月24-25日在松江附近发现并打开了她的儿子巴希略的棺墓。此外,在其旁还有另一个棺墓,墓主是一位身着上述锦袍的女性。上海《圣教杂志》1937年第5期报道了这一事实。参见F. Bortone, I Gesuiti alla corte di Pechino (1601-1813), cit.,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