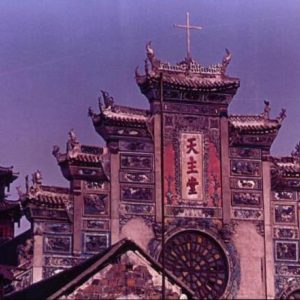很少有人能像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巨著《世俗时代》(L’ età secolare)中那样追溯我们当代失去信德的根由。这位加拿大哲学家将这一过程的起源追溯到宗教改革。通过推崇个人信仰,贬低圣事、神职和神圣事物,宗教改革终结了令人陶醉的中世纪,逐渐促成了另一种人文主义信仰的产生[1]。随着对“唯以信德为尊”和“唯以圣经为尊”的强调,改革者促成了信仰与理性的分离。这种分离随之被现代性两极分化。启蒙运动推动了这一进程的速度,它以自主的理性取代了启示。随后,科学革命使科学方法被确定为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
随着一系列的宗教和文化变革,现代性的世俗化程度日益加重,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灵修方式,特别是神操的实践。
背景
泰勒认为,启蒙运动之以自然神论取代历史上的基督教可以被视为一个走向当代无神论的“中间阶段”[2]。天主不再是一位有位格的天主,一个在历史上与人类和受造界秩序互动的主体,而是一位不具备位格的宇宙建筑师。宇宙因受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支配而由世俗科学所操纵。天启于是不再必要。通过强调观察和实证,科学革命倾向于对超验信仰的排斥。随着超性意识的丧失,即对神的意识的丧失,以及与传统宗教权威的逐渐脱离,灵修越来越聚焦于个人及其感受。宗教被作为一种制度化现实而受到排斥[3]。
现代性对理性的无限信赖及其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的能力将导致一种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反应,这已经很明显地体现于齐克果(Kierkegaard)、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思想家身上:他们反对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传统,认为我们是受无意识动力或经济规律影响的主体。20世纪的种种恐怖——其中包括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以及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造成的严重平民伤亡,种族灭绝,冷战期间的核毁灭威胁,艾滋病大流行,贫富差距,更不用说在21世纪夺走数百万受害者的新冠大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仅靠自主理性便能引导人类走向完美的幻想。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乐观主义反应,它更是一种感性,而不是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哲学。它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的元叙事,并倾向于赋予一切真理的陈述以相对性,认为它们总是受制于其揭示者的社会地位并以植根于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的权力关系为基础。由此,真理之概念本身也遭到质疑。
灵修
当然,灵修(spiritualità),亦或如今所说的灵修,并未能避免这些文化变革的沾染。对许多人来说,天主已不再具备位格,而仅仅是一种哲学原则或“超级力量”,比如当今新时代(New Age)思想中的“灵性”或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原力”。许多人将“属灵但无宗教信仰”引以为荣。有些人则更甚,他们完全摈弃灵性层面。
在西方,许多人正在脱离自己的宗教传统。这种现象通常被描述为无信仰者(nones)的崛起,他们是那些在被问及宗教信仰时回答“无特殊信仰”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无信仰者达26%,并且在白人、黑人、西班牙裔、男性和女性这些多数群体和全国各地区都仍在上升,不分教育水平。这一数字在年轻人中甚至更高:只有49%的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人)自称基督徒,而每10人中有4人是无信仰者。西班牙裔天主教徒的数量也在持续下降:从10年前的57%跌至如今的47%[4]。在英国,天主教徒出身的人中只有略多于半数以上的人仍然认同自己的这一身份。
圣玛丽出版社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日渐消逝》(Saint Mary’s Press, Going, Going, Gone)列举了三个原因以及分别与其相对应的群体来解释如此普遍的脱离关系。第一个类型是“受伤者”,指的是那些在家庭或教会中有过负面经历,遭受过创伤性事件的人,比如亲人去世、离婚、渐进性疾病或其他家庭危机。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影响个人信仰的事情归咎于天主。然后是“流浪者”,即那些由于认识不足或者因为与家人或同龄人分享的信仰或灵修团体疏忽责任而放弃信仰的人。这种情况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父母双方对信仰的热忱。如今的许多年轻人都成长于家庭成员均已失去信仰热忱的家庭,或者就许多天主教徒而言,在其家庭中,天主教更是一种文化现实,而并不关乎选择和投身。第三个类型是“持不同政见者”,是指那些与教会训导存在分歧的人,尤其是关于性行为、妇女和堕胎的问题。最后这个类型是最复杂的一个成分,因为许多人在反对的同时也对妇女的选择权给予支持[5]。
有趣的是,在对灵修的反思中,耶稣会前任总会长倪胜民(Adolfo Nicolás)神父如是定义了“肤浅的全球化”:“这个世界正变得非常肤浅。我们拥有比以往更丰富的信息,但缺少思考、反思和吸收信息的能力”。我们的依据是感觉、“新鲜”的信息或“捷足者先登”。即使是完全属于偏见或具有破坏性的信息,也照样会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而我们没有能力查清它是事实还是成见。同样的情况也正在发生于教会中[6]。我们应该将此视为一个真正的认识论危机[7],它已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灵修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问题是:于今,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神操和做神操的价值是什么?
在今天提供神操指导
自耶稣会复会以后(1814年),作为该修会生活特征的灵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禁欲主义实践和道德美德发展关注的主导。直到20世纪下半叶,在约瑟夫·德·吉贝尔(Joseph de Guibert,1877-1942)、米格尔·尼克劳(Miguel Nicolau,1905-86)、威廉·J·杨(William J. Young,1895-70)、卡尔·拉内(Karl Rahner,1904-84)及其兄弟雨果·拉内(Hugo Rahner,1900-68)等耶稣会士的工作基础上,耶稣会士才开始谈论以《神操》为基础的依纳爵式灵修[8]。
在这种变化中,可以回顾的例子包括以针对个人的避静取代传统的布道避静,或将省察这一概念重新理解为“良心的省察”,即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的存在,而不是列举各种挫折的原因或将信德理解为一种伸张正义的信仰。此外值得提及的是,对圣依纳爵的《与教会思想一致的规则》之理解向来基于以圣统制的教规进行推理的意识。教宗方济各有力地拓宽了我们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习安东(Antonio Spadaro)神父在他发布的访谈中把“天主的神圣信众”视为一个主体,意指“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天主位居其中。“因此,‘与教会思想一致’也不应仅限于与其圣统制部分相关的理解”。他补充道:“当信众与主教和教宗之间的对话进入这条轨道,并且是真诚的,那它是得到了圣神的帮助”。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信仰意识” (sensus fidei)和“信仰者的意识”(sensus fidelium)重要性的关注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断言,当天主的全体子民在信德中相携同行时,他们展现的是一种信仰中的正确无误性(infallibilitas in credendo) [9]。
我们认为,世俗文化已经取代了仍被许多人藐视的宗教文化,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涉及西方。为此,我们今天需要在一个更广泛的环境中提倡灵修。我们因此而不能简单地假设一种传统宗教文化。许多参加神操或退省的人并不熟悉圣经故事和记载,或者认为它们相当过时,不再具有说服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世俗文化,要么不了解教会的信仰和神学,要么拒绝接受它们。这并不是说我们建议可以撇开圣经的记载,而是说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以唤起今天参加神操者的想象和理解。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思考天主浩繁的化工,或是在进化过程中,或是在生命的活力中。天主的恩赐反映了超乎想象的善与美,而痛苦、不公正和暴力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带来的伤害则敦促我们成为门徒。
神操的结构建立于三个基本支柱之上。“原则和基础”提醒我们要在生活中将天主放于首位。关于“基督的神国”的默想向我们讲述门徒的身份,邀请操练者发现自己的圣召。“圣爱瞻想”是耶稣会在所有事物中寻找天主的原则之基础。在此,我们希望展示有关上述每一点的思考。
“原则和基础”
这个作为开端的默想非常名副其实。它提醒操练者其受造是为了“赞美、敬畏和侍奉天主”,并通过这种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对精神自由的召唤。对于那些对天主在自己生活中的存在持开放态度的退省者来说,这是在邀请他们思考深化这种关系的圣召,寻求给出更圆满回应的自由。
但其他操练者,特别是那些接受世俗文化教育的人,也许会认为天主的概念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陌生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议从宗教层面转到宇宙学层面。邀请他们默想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之广袤可以帮助他们感知天主的神秘,祂作为造物者的存在既隐蔽又亲密,既超然又内在,体现于我们所说的“受造界”中。此外,祂的伟大超越所有人的理解力。
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的宇宙始于大爆炸这一想象中的始点,由极其密集和过热的物质和能量组成,然后产生爆炸,形成无限微小的粒子,然后是原子和分子、气体,最后变成恒星、行星和星系,也产生了空间和时间。每个星系都是一个由恒星和恒星碎片、星际尘埃、气体和暗物质组成的完整系统,被引力固定在一起。随着星系之间不断的相互远离,宇宙也在不断地膨胀。在一些难得的夜晚,当看到自己头顶上群星璀璨的苍穹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宇宙的无限,根据科学家的估计,它们的数量着实令人震憾!根据圣咏作者的说法,天主制定了所有星辰的数目,并各按其类给它们命名(参见咏147:4)。我们的星系,即银河系,拥有1000至4000亿颗恒星和至少同样多的行星。而天文学家认为,银河系不过是我们可观察到的宇宙中大约2万亿个星系之一。
但是,组成这个宇宙的不仅是惰性气体、燃烧的恒星和死亡的行星,还有生命的脉动。在这些星球之一,即我们所说的地球母亲之上,大约45亿年前,原子和分子开始膨胀,发展成有生命力的细胞、微生物、细菌、氨基酸和植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动物,衍生了目前居住在地球上的约1万亿个物种,包括我们人类本身。
对于许多与我们最相仿的动物物种来说,生命是一场持续的生存斗争。为了能够应对,它们的天性中充满了可为捕食而杀戮的本能。圣咏诗人写道:森林里的野兽在黑夜中从洞穴里出来,四处狂窜,少壮的狮子怒吼着寻找猎物来充饥(参见咏104:20-21)。诗人描述了一个“在矜牙舞爪中染红”的大自然。这种进化型继承也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印记。
然而,即使在动物世界中,也有一种趋于团结、结合、交融的动力。许多动物自然倾向于集群生活,并通常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是牧群、兽群、羊群和鸟群。动物表现出的往往不仅是本能,而且还有情感、亲情的迹象,甚至是智慧:这些表达方式在人类身上会转化为一种圆满。母兽以惊人的温柔照料它们的幼崽,勇猛地保护它们,甚至能够为此而不惜牺牲自己。狗狗会欢天喜地地迎接主人的归来;它们喜欢玩耍,追着球跑来跑去,或者跳着抓飞盘。鼠海豚以玩耍为乐,它们跳出水面,有时还会摇着尾巴跳舞。社交媒体上充满了狗和猫成为朋友、一起玩耍或抱在一起睡觉的有趣视频。
就连树木也有社会生活,根据最近的研究显示,它们通过地下根系网络进行碳、水、营养物质、警告信号和激素的交换,即使不同种类的植物之间也是如此。这些资源从年长的树木流向更年轻和较弱小的树木,那些地下连接被分开的树木更有可能枯萎和死亡[10]。
我们自问:所有这些被称为“生命”的非凡能量来自何方?我们能否从这种团结的动力中学到什么?难道我们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宇宙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不过是偶然结果,而且人体也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原子、分子和微生物的随机组合?人的复杂性反映着宇宙的复杂性。像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这样的科学家认为,我们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单分子中的原子数量与大多数星系中的恒星一样多,而一只人眼所含的原子数量甚至超过已知宇宙中的恒星。
然而,许多科学家在他们的普遍体系中不愿意承认一种超越感性的智能,他们不会走出可验证的现实来质疑这一界限之外可能存在的事物。另一方面,那些有信仰的人相信,在复杂的宇宙背后,事实上,在其复杂性之中,在我们自己的精神中,有一位天主,祂的创造活动不断地维持着一切存在,包括我们自己,并继续向我们伸出援手:这位天主在耶稣身上显示,就像一位充满爱的父亲,一位阿爸。“原则与基础”正是要求我们对这一点进行反思。
“基督的神国”
对基督神国的默想被奇怪地安排于第一周操练的结尾和第二周操练的开始之间。我们更乐于以默观“道成肉身”作为第二周的起点,然后转向对王国和基督君王的号召的默想,这自然与紧接着的对基督生命的关注相连贯。对“道成肉身”的默观以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单纯的图像和语言提出,邀请操练者思考三个神圣的位格俯视大地上的各种景况及所有悲剧和暴力,然后派遣第二位屈尊为人,以拯救人类。
对神国的默想以思考世间君王的号召为起点,然后敦促操练者想象基督邀请每个人加入祂的使命。祂的条件具有挑战性:“谁愿跟随我,该同我一起劳苦工作,将来也要同我一起享受光荣。”(《神操》 95)。这个邀请可与世间君王的挑战相呼应,要求那些愿意服从于他的人“吃喝穿戴,都跟我一样;还该和我一样,白天工作,夜间警惕。这样分担我的劳苦,将来也要分享我胜利的果实”(《神操》 93)。
但是,作为依纳爵提出的默想对象,在所有的悲剧性和令人悲痛的情况中,三位一体视线中的使命及世间景况是怎样的呢?只需加入一点想象力,就大可使它变得更为具体。今天,信德的最大障碍,也就是与基督的使命相对立的障碍,是存在于世界上的诸多痛苦、不公正和对无辜者的暴力。
让我们回顾20世纪的种族灭绝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系统性杀害,斯大林统治下的乌克兰人民以及希特勒时期的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还有柬埔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其他无辜受害者,其他屠杀和种族清洗。我们还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丧生的数百万平民,从城市的大规模轰炸到广岛和长崎的核破坏。我们也想到了目前乌克兰战争的野蛮行为,集体坟墓,被轰炸的医院,以及被侵犯和屠杀的平民。我们想到数百万的男女和儿童被埋在农场和田地里的地雷炸伤致残,想到许多国家那种玩世不恭地利用政治权力中饱私囊,想到那些在无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想到数百万滞留在难民营中缺少适当教育的难民儿童。统计数据虽然不涉及个人,但在其赤裸无情中却如此令每一个人感到震惊。
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之间的差距持续加剧。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数据,在2019年中,因战争、暴力、气候变化和迫害而背井离乡的移民和难民人数达到了近7080万人的历史最高点并在继续增长。数以千计的人因超载船只的倾覆而葬身大海,或在徒步移民时成为掠夺行为的受害者,而号称土狼的人口走私者则从中牟取暴利。在亚马逊地区,由于因商业利润而被蓄意烧毁的雨林,原住民已经被疏散。另一个问题是现代奴隶制,它使大约4000万男子、妇女和儿童受到奴役,成为强迫性劳动、早婚或债务的受害者。此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女孩,她们大多数是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受害者中包括难以计数的儿童,他们被卷入了我们的城市暴力、枪击和毒品冲突。还有一些是受到身体或性虐待的人,虐待他们的是亲属或被认为值得信赖的成年人,甚至是神职人员。让我们再想一想花费于战争武器、恐怖主义威胁、色情和堕胎行业上的数十亿美元。这就是基督君王履行其使命的世界,我们必须追随祂的地方。
“获得爱情的默观”
神操以“获得爱情的默观”结束。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默想,提醒操练者如何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达爱,并建议以献己诵(Suscipe)表达的个人奉献来结束四个建议中的每一端。
第一端要求操练者回想所受的诸般恩惠。这里应该投入最高程度的想象力和情感。有些恩惠是关于宇宙的:我们之前考虑的浩瀚而美丽的宇宙。其他恩惠是神学的,是救赎,是恩宠:如卡尔·拉内(Karl Rahner)所描述的,天主的自我启示,我们的信仰,圣事。还有的恩惠是个人的,来自家庭、朋友、经历、人们、那些曾经爱过我们和我们爱过的人。其他的恩惠是技术性的,比如互联网,它使我们能够获得诸多信息。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可能会在其中看到一个全球性的神经系统。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兴奋和愉悦,使我们以赞美和感恩的行动面向我们仁慈的天主。
第二端要求我们观察天主如何居住于祂的受造物中,根据不同物种和种类,赋予它们生命、感觉和智慧,使我们成为祂临在的宫殿。天主临在于天上的星辰中,临在于大地的美丽和覆盖它的草木植物中。当面对如此多的美景时,我们往往能感知到这一点,满怀好奇和敬畏。大自然为它的创造者歌唱。
第三端要求我们看到天主在祂的恩惠中工作。依纳爵在这里的语言不仅是比喻性的。如果创造是在圣言中并通过圣言发生的(参见若1:3;哥1:16-17),那么当基督把一切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并将其提交给天父时,创造也将发生,以至“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格前15:28)。德日进所说的“天主的缓慢工作”[11]就发生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伊利亚·德利奥(Ilia Delio)看到的是天主“神圣的、持续的创造、救赎和圣化整个宇宙的行动”[12]。我们可以想象,天主的创造工作是如何在生命的能量中变得日渐明显,这种能量不断扩展,克服种种障碍,迸发出无数的类型和品种。
在第四端中,我们被要求反思天主的所有恩惠是如何从上降下的,我们有限的力量是如何来自天主无限的至高权力。生命绝不能沦为单纯的化学作用或神经反应。人不只是一台不具备精神和道德参照的机器,而是由与生俱来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模式和生物化学规律组成。智能不只是反射和算法。多玛斯·阿奎那将其描述为对天主的非创造之光的参与。正义、善良、怜悯、仁慈和爱的恩惠只是在神性中对其自身完美性的有限反映。有多少次,我们会被一张孩童的脸庞、一个人的身体、一个自然景象或一件艺术品的美所震撼。无论是作为比喻还是从字面意义上,我们都已经认识到至高的善良和仁慈,正义战胜邪恶,以及赋予生命的爱的时刻。
因此,让我们感谢主,并诵念献己诵:“主,请祢收纳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理智,和我的整个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祢所赏赐的;我愿完全奉还给祢,任凭祢随意安排。只将祢的圣爱,和祢的圣宠,赏赐给我,我便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神操》 234)。
结语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竭力提供一些建议,旨在拓宽操练神操者的想象力,以提供更好的陪伴。由于他们中许多人的世俗文化背景不仅塑造了其宗教想象力,而且并不总是积极的,许多人对信仰和教会的教义的了解只是留于肤浅。
与此同时,今天我们自己对神操灵修的理解也与前几代人不同。在不偏离支持神操和标记操练的圣经记述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反思适当的方式来发展操练者的想象力,以加深他们的理解。
- 参阅C. Taylor, L’ età secolare, Milano, Feltrinelli, 2009, 106. ↑
- 参阅同上,346。宗教归属的急剧下降并不完全是一个西方现象。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在201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年轻人比其他年龄组更倾向于无宗教信仰的现象不仅在欧洲和北美,而且在19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的14个国家出现,包括墨西哥。这一趋势在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太明显,但韩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是在宗教实践方面显示出年轻人与其父母之间存在最大差距的国家(Pew Research Center, «In U.S.,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Continues at Rapid Pace», settembre 2019)。 ↑
- 参阅同上,635-640。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世俗时代”,这将同时考验绝对化的科学观以及信仰与理性共存和相互学习的必要性。这一概念一般被归功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无论如何,大众和政治文化至今仍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
- 参阅Pew Research Center, «In U.S.,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Continues at Rapid Pace», settembre 2019. ↑
- 参阅Cara, Going, Going, Gone! The Dynamics of Disaffiliation in Young Catholics, Winona, MN, Saint Mary’s Press, 2017, 13-24. ↑
- 倪胜民神父在Heverlee的思考,视频;全文见F. Brennan (ed.), Shaping the Future: Networking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for a Globalizing World: Report of the Mexico Conference, Association of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prile 2010, 7-21. ↑
- 信息过载不一定是一种祝福。正如 倪胜民神父所观察到的,它并无益于内在性或反思。社交媒体令人痴迷,而且往往含有自恋情节。我们变得执迷不悟,社群归属感日渐淡泊。年轻人在Instagram上贴满了数百张自己的照片,在TikTok上无休止地曝光自己。因为公众访问轻而易举,现在每个人都大可耀武扬威。我们受到图像及个人意见的轰击;各种声明无需通过任何检查。很少有人再花费时间去阅读报纸或杂志上的文章,人们的认识莫过反映个人观点的台词。 ↑
- 参阅J. W. O’Malley – T. W. O’Brien, «The Twentieth-Century Construction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A Sketch», i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52 (2020/3) 18. ↑
- A. Spadar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13 III 449-477; cfr Commissione teologica internazionale, Il «sensus fidei» nella vita della Chiesa, 2014. ↑
- 参阅F. Jabr, «The Social Life of Forests»,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6 dicembre 2020, 34. ↑
- 摘自德日进的祈祷文,Paziente fiducia。 ↑
- I. Delio, Christ in Evolut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8,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