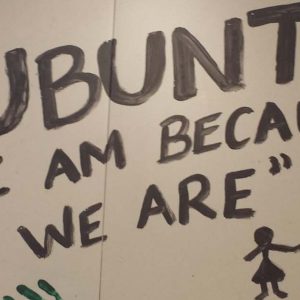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22年12月31日在梵蒂冈山丘上的教会之母(Mater Ecclesiae)隐修院安息主怀,享年95岁。他在放弃教宗牧职后退居于此,在引退和祈祷中度过了其漫长人生最后的年头。此间,他的一次重要破例出行是于2020年6月18日至22日前往雷根斯堡(Regensburg),在他最心爱的兄长格奥尔格·拉青格蒙席去世的前几天前往探望并做最后的告别。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于2016年6月28日在宗座大楼克莱孟厅为其晋铎65周年纪念而举行的庆祝活动,教宗方济各也出席了庆典。教宗方济各曾多次前去探望他,不少朋友和来访者也能够接近他,并通过社交媒体发送消息和图像,以使我们能够继续感受到他谨慎而警惕的形象的陪伴;有时候,他也会以信件或简短信息的形式答覆,其中无一例外地展现出他的善良、睿智和强烈的灵性生活。涉及重要议题的写作则相当罕见。
漫长的人生阶段:从巴伐利亚到罗马
若瑟·拉青格于1927年4月16日出生在巴伐利亚的马克特尔(Marktl am Inn)镇。那是在圣周六的清晨,他在同一天早晨受洗,正如他所叙述的那样,“所用的是刚刚受祝福的水,因为那时候,‘复活节守夜礼’是在星期六早晨举行。[……]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很感恩,以这种方式,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圣体圣事的神秘中,因为这只能是一个祝福的标志”[1]。若瑟出生于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传统的普通巴伐利亚家庭。他的父亲也叫若瑟,是一名警察;母亲玛丽亚是一位家庭主妇,但有时也会做些厨师的工作,以满足家庭开支所需。他在家中排行第三,是最小的孩子,比他年长的有大姐玛丽亚和哥哥格奥尔格[2]。
若瑟的童年基本上在一种平凡与安宁中度过。全家人随着分配给他父亲的工作任务而搬迁于巴伐利亚的不同地方。在马克特尔镇之后,他们于1929年迁往蒂特莫宁(Tittmoning,这里对若瑟来说始终是童年梦想和快乐时光之乡),于1932年搬到阿绍(Aschau),于1937年到了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12岁的若瑟于1939年在那里进入总主教区的修道院,他的哥哥格奥尔格也在他之前于那里就读。那是希特勒执政的年代,若瑟感到了空气中即将来临的风暴,但在巴伐利亚省及其家庭浓郁的天主教环境的保护下,他闯过了这一关。那里的反纳粹态度虽并不激进,却十分鲜明。
随后,纳粹主义的到来直接殃及若瑟本人。修道院在他入学后不久便被征用,他被迫登记加入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但未曾参与它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6岁的他被分配到慕尼黑市防空部队:虽然是一名士兵,他却能够和其他修生一起继续学习,在该市的一所高中就读。
他于1944年9月退出防空部队,被派往布尔根兰(Burgenland,位于奥地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交界处)服役,并在此后因感染而被送往特劳恩施泰因军营。在德国崩溃前最后几个月的混乱中,他逃役返回家中,但在美军到来时,他被当作战俘同其他50,000人一起被押往乌木(Ulm)附近一个条件极其恶劣的露天大监狱。6月16日,他在最终获释后重新回到家中。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他的司铎圣召坚贞不渝。尽管当局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但若瑟在慕尼黑和弗莱辛(Frisinga)重拾学业,以成熟的灵修分辨为圣职做准备,并在文化和灵修均出类拔萃的人物的陪伴和指导下以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投入了钻研神学的世界。这是他开始熟悉圣奥斯定思想的时期,这位圣人将成为他一贯最为热衷的作者和基本依据,但他也兼顾当代伟大神学家的精彩著作,例如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
1951年6月29日,格奥尔格和若瑟在弗莱辛主教座堂从慕尼黑总主教弥额尔(Michael von Faulhaber)枢机手中领受铎职。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虽然热衷于神学研究和教学,但对若瑟来说,铎职始终是他在喜乐、感恩和巨大责任感中所活出的圣召之首要层面,并同时将礼仪服务、圣道和牧灵关怀与对文化的反省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晋铎后的新司铎被分配到慕尼黑的一个地区做一年的堂区工作,身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本堂神父。他以极大的决心和兴趣完成了这项任务,以至于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他称其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3]。因此,如果将拉青格的个性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冷漠或抽象,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搏动于他心灵深处的是牧灵的敏感度。然而,研究和学术生涯的道路似乎更适合这位显然在这一领域天赋异禀的年轻人。
通过1953年关于圣奥斯定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他如愿被授予讲师职务。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中一段几乎悲剧性的艰难时期,原因是与慕尼黑大学的两位权威教授,即他的导师戈特利布·索恩根(Gottlieb Söhngen)以及迈克尔·施马斯(Michael Schmaus)就他关于圣文都辣的论文发生了公开冲突。这篇论文最终被接受,拉青格于1957年获得讲师职称。然而,这些张力将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位此前已因其出色成果而被广为称道的年轻神学家遭遇了新经历,他受到的批评之严厉甚至从根本上危及到其职业生涯。抛开争论的作用不谈,他在最后明智地指出, “羞辱是必要的[…]。对一个年轻人有益的是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接受批评、被迫经历一段挫折” [4]。
由此,拉青格成为教授。这是他人生历程中持续了近二十年的一个重要阶段。最终,这一时期使他能够活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召叫,从事他渴望做的事情。不过,这个阶段也经历了许多不同时期。在担任弗莱辛大学信理神学和基本神学讲师之后,他应邀担任的第一个讲席是自1959年至1963年在波恩大学讲授基本神学;他后来转入明斯特大学(1963-66)讲授信理神学,后来又在图宾根大学(1966-69)、最后还在雷根斯堡大学(1969-77)任教。他出色的大学教学质量内容深刻、阐述清晰、语言优美准确,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学生们为听他讲课而挤满课堂。对于这位教授“出身”的教宗,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些品质余音绕梁,并在阅读他的文件、聆听他的讲话、教理讲解及讲道的时候在更为广泛和普遍的层面上欣赏到。
在这一时期,拉青格人生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发生了:他以科隆教区年事已高的若瑟·弗林斯(Joseph Frings)枢机的神学顾问身份出席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当大公会议宣布召开时,拉青格正在科隆教区的波恩担任教职;此后不久,他在出席一个关于大公会议神学的重要讲座时崭露头角,迸发出引人注目的火花。弗林斯虽然几乎失明,却将是梵二会议上的一位主角,是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在内的中欧和北欧主教当中的一位领导人物,他将在大公会议中扮演着引导会议方向的决定性作用。30岁出头的拉青格成长于与罗马学院有别的学术环境,他陪同弗林斯并为其准备回忆录和发言稿:这些文字将留芳于世[5]。
然而,除了对制定文件的贡献以外,大公会议期间在罗马的驻留为这位青年教授创造了一个难逢良机,使他结识了当时的主要神学家拉内(Rahner)、德吕巴克(de Lubac)、孔加尔(Congar)、舍尼(Chenu)、达涅罗(Daniélou)、菲利普斯(Philips)等人,并在从内部体验本世纪最大教会事件的同时深深感悟到教会的普世性及其所面临的当代挑战。他的视野延伸到世界的边远地区,神学及牧灵思考由于面对着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不再容许将自己封闭于短浅的局部视角中。
然而,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任职大学的频繁更换便说明了这一点。在激动人心和富于创意的大公会议期间,教会和神学领域也出现了反面的发展和分化。有关神学家关于教会职能的争论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德国。因此,虽然鼓励拉青格迁往图宾根的正是汉斯·孔(Hans Küng)本人,但这两位神学家的路线却因发生分歧而不可避免地相互疏远。在某种程度上,拉青格不得不认识到,对于孔和某些人,“神学不再是天主教会对信仰的诠释,而是建立自我,它之所能及所是的基础上。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天主教神学家来说,这并不与神学相符”[6]。
正是在这一恰逢1968年学生骚乱彻底扰乱了大学生活的背景中,拉青格告别了图宾根,前往更安静的雷根斯堡。但这并不等于那是轻松或没有收获的岁月。恰是在1968年,《基督宗教导论》出版了:这部著作诞生于为所有院系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其结构以对“使徒信经”的评论为基础。这始终是拉青格著作中阅读率最高的一部成功之作,不仅被翻译成20种语言,而且至今仍在不断重版。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内容深刻、语言淳朴,两者间的对比引人入胜,使其即使在学术圈之外也广为人知。 拉青格强调基督信仰的个体性本质:“世界的意义是 […]‘祢’ […]。 因此,信仰就是找到一个给与我支持的‘祢’,祂在人与人之间每一次相遇的不完整中赋予我坚不可摧的爱的承诺,这种爱不仅追求永恒,而且将它赐予我们”[7]。随后几年中,他在雷根斯堡的教学活动不仅体现于教程中,而且体现于更密切地关注那些选择他作为博士生导师(“Doktorvater”)的博士生研究。直到他的教宗任期,拉青格将继续以令人钦佩的诚挚对待由此而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学生圈( “Schülerkreis”),见证了师生之间所建立的异常深刻的文化和灵性关系。
然而,正值半百之年的拉青格教授在学术和文化上达到炉火纯青之际,慕尼黑总主教、德国天主教无可争议的领袖朱利叶斯·邓普纳(Julius Döpfner)枢机因心肌梗塞而猝死之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保禄六世偏偏向他提出接替邓普纳,一个使他为难的服从。应该将德国的主要主教区委托给文化造诣超群的人士,这种想法对于历任教宗来说并不稀奇。拉青格是一位公认的权威神学家,他在后大公会议时期的紧张局势中表现出对教会的深厚依恋,同时也是一位“巴伐利亚爱国者”——正如他本人所自称。对这位教授而言,接受任命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但服务的责任意识要求占了上风。1977年5月28日,他被祝圣为主教。随即,保禄六世又擢升他为枢机:6月27日,拉青格在罗马领受了枢机方帽。
作为他的主教座右铭,他选择了真理的合作者(“Cooperatores veritatis”),这句话引自圣若望三书(1:8)。很难找到更好的一个词语来表达作为神学家对研究和教学的承诺以及作为主教对训导和牧灵指导的承诺之间的连续性。这也将适用于他此后的承诺,成为他终生的辉煌座右铭!鉴于对总教区牧灵关怀的承诺,作为慕尼黑总主教将是紧张的工作,但也相当短暂。那一时期正逢“三位教宗之年”和两次选举教宗会议(1978年),然后是教宗沃伊蒂瓦的当选及其对德国的首次访问(1980年),而这次访问恰好于慕尼黑告终。若望·保禄二世在此之前便已经认识拉青格并对他高度推崇。他指定拉青格为1980年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议题组长(relatore),这是新教宗任期内的首次世界主教会议,并立即向其表明希望他到罗马作信理部领导的愿望。拉青格起初表示反对,但由于教宗决心已定,他于1981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部长,并于1982年3月前往罗马赴任。
枢机部长
这个新阶段将相当漫长。拉青格将是若望·保禄二世23年中最信任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教宗绝对不愿失去他的贡献,直到这一历史上为期最长的教宗任期之一结束之时。教宗和部长之间亲密的关系建立在相互敬重的基础上,即便两人性格不同。拉青格的形象无疑是构成这一时代教会生活特征的一个基本因素,他忠实地诠释教宗的路线,为若望·保禄二世的教会管理提供了极具深度的神学支持。这令人情不自禁地谈起一位伟大教宗与一位伟大部长之间难能可贵的“惊人配合”。
拉青格枢机在这些年中完成的工作令人肃然起敬,这也要归功于他指导合作者团体工作的能力:他倾听他们的意见,以非凡的概括能力指导他们的贡献,使得这些文件与其说是其个人工作成果,不如说是整个组织的努力。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大公会议后,教会内部神学视域中的争论也很激烈。
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无数事件中,我们可以强调三件突出的大事。首先,教会在1980年代前半期对解放神学这一主题的干预。教宗极其关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拉美神学思潮的影响,部长与他意见一致,并勇敢面对这个微妙的问题。
两个著名的指示(Istruzioni)由此而生,它们旨在反对消极的漂移(第一个,1984年)和肯定积极方面的价值(第二个,1986年)。在由此引起的反响中既不乏批评,特别是针对第一份指示,也不乏激烈的争论,包括个别引起争议的神学家(最著名的是巴西的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的具体案例。对于拉青格,尽管具有被公认的文化修养,却同样无法逃脱信理部负责人以严厉的审查员、正统的守护者、神学研究自由的主要反对者而闻名的共同命运;此外,作为德国人,他还被冠以Panzerkardinal(装甲枢机)这一不友善的绰号。
多年后,信理部的另一份文件又掀起了另一波批评的浪潮,那就是2000年大禧年期间就耶稣基督对所有人救恩的中心地位而发布的《主耶稣》(Dominus Iesus)宣言。这一次,被触动并作出回应的主要是那些专致于普世关系以及与其他宗教对话的领域。无疑,在这种情况中所采取的立场同样完全契合若望·保禄二世的意愿,即保护教会信仰的某些基本点,使其免受误解或偏离的严重影响。
第三项工作同样引起了许多初期的争议,但最终赢得了广泛的共识和成功,那就是编撰新《天主教要理》这一真正的巨大努力。1985年的世界主教会议要求以适合当代的语言制定对整个天主教信仰有组织的阐述,反映大公会议的革新。教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拉青格枢机和一个由他主持的委员会。在经历了一个相当强烈的神学和教会争议与张力的时代之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这项工作便于1992年以一种令人折服的方式告终,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唯有以一种对信理和整个基督信仰生活领域有组织和综合性视域的卓越才能,方可指导并完成这项工作。此外兼备的还有对当代期望的敏感度。以上这些不正是我们25年前在《基督宗教导论》的作者身上认识到并钦佩不已的品质吗?《要理》可能仍是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任期中在信理方面最重要的积极贡献,是教会生活可靠的宝贵工具。正因如此,教宗方济各经常提起它。
教宗与教宗任内的“最高优先事项”
于是,我们来到了若瑟·拉青格漫长道路上的倒数第二个、但在教会意义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像前两个阶段一样出人意料,但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后,不同的原因将视线引向他这位可能的继任者,包括:十分融洽的长期密切合作;卓越的智慧和灵性品质;毫无任何使他凌驾于他方之上的权力野心;最后还有,作为枢机主教团主席,他以从容的应对力主持各项筹备和举行选举教宗会议的活动和仪式。尽管他已年迈,但延续性的选择很快便占了上风。4月19日,78岁的若瑟·拉青格当选天主教会的第265位教宗,他选择了本笃十六世这一名号,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人们宣称自己是“天主葡萄园里简朴而谦卑的工人”。
尽管新教宗年事已高,但在持续了近八年的教宗任期中,他将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进行密集的活动。除了在梵蒂冈举行的礼仪庆祝及公众接见等“常规”活动外,我们还可以回顾他遍及五大洲24个国家的24次国外牧灵访问,其中多次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29次意大利牧灵访问;五次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其中包括关于圣体(2005年,经若望保禄二世召集)、关于天主话语(2008年)和关于促进新福传(2012年)的三次常规会议以及两个特别会议,即非洲会议(2009年)和中东会议(2010年),每次会议之后(2012年的最后一次除外)都会相继颁布一份重要的宗座劝谕。
值得注意的其他主要训导文件是三部通谕。此外,尤为重要的是2007年五旬节的《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徒信函》。另外值得回顾的是,本笃十六世意欲以各种“年”赋予他对教会的牧灵引导以一致性及导向。在完成由其前任开启的“圣体年”之后,他又相继宣布了“保禄年”(2008年6月28日至2009年6月29日,纪念宗徒诞生两千年)、“司铎年”(2009年6月19日至2010年6月11日,纪念阿尔斯本堂神父逝世150周年)以及最终的“信德年”(2012年10月11日,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50周年)。至于最后的信德年,教宗因辞职而未能亲自完成,为此,应该观察一下他本人在回答Seewald的提问时所言。Seewald的问题是:“回想起来,您认为您教宗生涯的突出标志是什么?”。本笃回答说:“我想说的是,‘信德年’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即:重新更新信德,从中心开始生活,以信德的活力,通过重新发现基督来重新发现天主,也就是说,重新发现信德的中心地位”[8]。
这些话直接将我们引向对教宗任期间优先事项的思考,并以此为关键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本笃在一份相当特别、充满激情和强度的文件中明确谈到了这一点。那是2009年3月10日的一封致主教们的信函,是在取消追随勒菲弗(Lefebvre)主教的主教们开除教籍的法令及“威廉森事件”后对他的批评和攻击中撰写的,他几乎意于在信中对其教会管理“进行理性解释”。“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大地上的广大地区,信仰就像找不到滋养的火焰一样面临着消亡的危险,高于一切的优先事项是让天主显身于世,并向人们打开通向天主的道路。这不是指通向任意一位神,而是通向那位在西奈山上说话的神;那位天主,我们在爱到底的驱使下认识了祂的仪容(参见若13:1),那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耶稣基督”[9]。
教宗本笃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与他此前的整个生活相一致的优先事项,其治理风格将被尖锐地描述为“训导式治理”。正如他本人所言:“我来自神学,我知道我的力量,如果我真的拥有某种力量的话,那就是以积极的形式宣扬信仰。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首先想从神圣的圣经及传统的圆满性出发进行教导”;与此同时:“有必要进行更新,我试图在对信仰的现代诠释的基础上带领教会前进”[10]。
不难看出,他如何以符合这一路线的方式对其通谕进行主题的选择和展开。本笃有意限制通谕的数量,并愿意将它们优先贡献给神学美德,即关于爱德的《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2005年);关于望德的《在希望中得救》(Spe salvi,2007年);关于信德的《信德之光》(Lumen fidei,未完成,将“死后出版”见光,由其继任者接手并完成)。
本笃关于爱和希望的论述非常深刻地涉及到这些词语在当代文化中的诠释方式和它对基督信仰和见证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可以从信仰的核心涌现的答案,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爱的至高意义的丧失以及在邪恶力量前陷入绝望的诱惑。
《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2009)同样属于教会社会训导的脉络,它阐明了基督信仰通过对爱德的具体承诺而对人类当今所遭受的严重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的回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教宗所颁布的世界主教会议常规会议主题与上述优先事项之间的一致性,即“教会生活和使命中的天主圣言”及“传播基督信仰的新福传”主题。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观察是,教宗本笃并没有将参与罗马教廷改革视为己任;尽管如此,他还是做出了一个革新的决定,即:建立一个专门致力于“促进新福传” 的新部会。
“最高优先事项”的第二个方面显著地体现于本笃十六世教宗任期内一个独一无二的元素中,必须引起关注,那就是:不是任何神,而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天主。拉青格自2003年起开始了一部关于耶稣的巨作,作为一个信徒和一个神学家,他在寻找“ ‘上主的仪容’(参见咏27:8)的个人”历程中感受到撰写这部著作的召叫[11]。这项工作对他来说似乎很紧迫,这主要是因为他内心日益增长的顾虑是现代解经方法会导致我们失去与耶稣本人鲜活的关系。
当选教宗后,拉青格并没有放弃这项工作,而是把它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将自己教会管理事工首要事务以外的所有“自由”时间全部投入这项任务,并如愿已偿地完成了它。他强调说,“这决不是一种训导行为”,其结果可供自由讨论和批评,但是,作为必须“坚固他的弟兄们”的伯多禄,他的研究和他个人的信仰见证对整个教会具有巨大价值,他心中非常清楚这一点。撰写这部关于耶稣的书实际上伴随着他的整个教宗任期[12],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他的一个内心世界。本笃十六世表示,他被深深地卷入这项工作。当Seewald向他问及:“是否可以说这项工作是您在教宗任期中不可替代的能量之源?”。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对我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不断从源泉深处汲水”[13]。
本笃十六世对教会礼仪的极大关怀也直接源于“最高优先事项”。一个真正的关注是使礼仪在团体和信徒生活中具有应有的地位,使其维护以与基督耶稣相遇为中心的庆祝活动的尊严。因此,在本笃十六世的意图中,没有怀旧的复古情怀,而是对教会生活一个基本层面的关怀。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应该看到他为避免传统断裂而付出的努力,这表现在《历任教宗》(Summorum pontificum,2007年7月7日)手谕重新允许以大公会议改革之前的罗马礼仪作为举行弥撒的“特殊形式”。
但在这一背景中,我们首先希望回顾的是在伟大的守夜祈祷中将朝拜圣体纳入世界青年日的重点活动项目这一成功的直觉:对于一个巨型青年节庆聚会,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逆水行舟”的创举,但它却得到了科隆、悉尼和马德里的数十万名青年参与者的极大欢迎和支持。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静默和灵性时刻是整个教宗任期中最美最强烈的时刻。这是本笃为世青会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大变革。
在谈到他的教宗任职时,本笃十六世补充说,天主的首要地位“带来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必须将信众合一铭记于心 […]。为共同见证基督信仰而努力因此被列入最高优先事项。除此之外,所有信仰天主的人都需要一起寻求和平,努力拉近彼此的距离,以便共同走向光明之源,而这正是宗教间对话[14]。本笃十六世在许多场合中表达了他坚定不移的普世承诺,其中他在牧灵访问期间的会晤依然令人难忘,包括在伊斯坦布尔与君士坦丁堡与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会晤(2006年),在伦敦与英国圣公会首领罗恩·威廉斯会晤(2010年),在埃尔富特著名的马丁·路德隐修院与路德派的会晤(2011年)。
在这里,本笃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回忆了路德的重大问题:“我怎样才能拥有一位仁慈的天主?”,以挑战大公教会的对话,在走向、尤其是回归信仰根源的同时寻求合一,而不是留于表面。一个微妙的时刻是宗座宪章《圣公会的结合》(Anglicanorum coetibus,2009年11月4日)的颁布,教宗在其中确立了欢迎英国圣公会信徒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团体要求加入天主教会的规范[15]。推动教会合一的服务还包括本笃十六世为重新建立与“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勒菲弗主教追随者的完全共融而作出的慷慨努力,这将使他付出承担不少批评和困难的代价,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获得成功的桂冠。
在其教宗任期内,与其他宗教对话领域中不乏艰难时刻:与犹太人,特别是在“威廉姆森案”以及为庇护十二世列真福品案而颁布的“英勇美德”法令之时;与伊斯兰教,特别是在雷根斯堡演讲时,其次还有复活节晚上埃及知名记者麦迪·阿拉姆(Magdi Allam)的洗礼。然而,拉青格毕生与犹太教对话的明显努力及其对伊斯兰教尊重与赞赏的态度同大公会议路线一致,这使他战胜了误解和困难。在教宗任期结束时,本笃十六世步若望·保禄二世前期使徒访问芳踪,除哭墙以外,他还访问了多达三座的犹太会堂(科隆、纽约公园大道、罗马)和三座清真寺(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安曼、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
与文化对话:“开放的理性”
在我们的时代,宣扬耶稣基督的天主意味着与当今文化对话。若瑟·拉青格总是无畏地将其付诸于实践,德国大学神学系的生活插曲及其讲座后的讨论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准备。他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慕尼黑天主教学院的对话(2004年)仍然著称。天主教传统始终坚持人类的理性价值,这不仅符合天主是爱的愿景,而且与天主圣言相符。
这位神学家教宗认为,在此基础上,甚至可以与不认同基督信仰的人寻求相遇点和共同点。他坚持以人类理性力量寻求真理的主题并为此而反复论证相对主义及其当代的“独裁”。
本笃十六世教宗任期内那些最著名的讲话可以在这一视域内得到解读。他在雷根斯堡大学(2006年)展示了“违背理性的行动与天主本性相悖的信念”,并将理性视为反对为宗教暴力辩解的必备良药;在巴黎伯尔纳多学院(2008年)回顾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包括对人的尊严的肯定,最初与中世纪隐修士对天主的探索有关;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国会大厦(2010年),他坚持认为,宗教信仰不能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而被归入私人空间,因为它对伦理和多元化的贡献不应被视为造成困难的原因,而是建设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柏林国会大厦(2011年),他警告说,局限性和实证主义的法律观会破坏法律的自身根基,而向超性 “开放的理性”有助于建设人的城市,发展令人信服的国家观念,这是我们用以克服激进的无神论或激进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观念等相互对立的挑战所需要的观念。
因受召认识和热爱真理而能于探索的“开放”及“扩展理性”的观念是本笃十六世思想和讲话中一个恒久的特征。正是理性不允许将自己封闭于科学的纯经验性视域和纯数学语言所强加的局限中,而是能够对人类、对哲学和道德、对生死的意义、对超性以至对天主进行更广泛的思考;因此,它不会冒着除了功能眼中旁无他物的风险将自己封闭起来。
“封闭的”理性“好似没有窗户的混凝土建筑,我们在其中自制气候和光线”[16]:最终,人类将被窒息,与自然的关系将仅由技术权力的活动操控,这种关系具有毁灭性。正是应该以这个视角来解读教宗任期富有创意和成效的倡议之一,即“外邦人庭院”:它是一个向所有人,包括非信徒开放的对话空间。这一观念被宗座文化委员会以创意加以采纳,并将其联结到许多不同的方向。
并非所有人都会接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建议: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因反对而决定放弃原定于2008年1月17日对罗马大学“La Sapienza”的访问。这一事件仅是“开放”和“封闭”理性之间选择问题的一例,但对话建议的价值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困难和危机
本笃十六世在其教宗任期内遇到了不同的艰苦时刻,这些时刻常常被媒体界以不太友善的态度强调。对它们进行回顾理所应当。按时间顺序,首当其冲的是他在雷根斯堡大学演讲中的某些措辞在伊斯兰世界内引发的一个强烈的负面反应浪潮(2006年):多亏一系列澄清性干预以及最终对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的访问,这场危机才被克服。另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是由于对上文已经提到的撤销对包括威廉姆森在内的追随勒菲弗主教的四位主教逐出教会的反应,这是一个真正的意外事件,因为教宗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拉青格在2009年3月以著名的《致主教信函》对这一危机作出回应。另一个引起许多议论的插曲是教宗在飞机上与记者谈到关于安全套的使用和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时所说的一句话(2009年):这句话的措辞不尽如人意,但在谈话的语境中极易得到很好的解释,然而,事与愿违,许多人倒是趁势抓住了一个攻击教宗的机会,这些人出于对教会蒙昧主义的成见而认为教会对人的罪负有共同责任。
但是,教宗任内的真正十字架是神职人员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事件。这个问题在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宗任内后期已经“爆发”,信理部部长不得不深入处理,但在其整个教宗任内,这个问题继续以悲剧式的显著性浮现。虽然不便于此一一历数其进程,但我们认为,教宗拉青格处理此事的方式应该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功绩。他不仅作出了谦逊、透明和严谨的个人见证,而且还为教会的管理和牧灵提供了一系列基本准则和法律规范:从承认责任到与受害者的个人接触、请求宽恕、承诺介入查明真相及制裁罪犯、预防和培训活动,还有在教会和社会中发展一种真正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文化。在他亲自参与的见证中,尤其引人注目是那些在他所访问的国家中(美国、澳大利亚、马耳他、英国、德国)应当地主教要求而与被侵害者进行的感人会晤。对于这一悲剧性问题的回应方案,最完整、最有组织的体现是他在2010年3月19日《写给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牧函》,这封信的价值显然不仅限于它所面向的这一个国家[17]。
教宗任期最后阶段中另一个令人痛心的复杂事件以梵蒂冈机密文件外泄(Vatileaks)之名而被载入史册:来自梵蒂冈的机密新闻及文件被泄露和出版,从而助长了一种不断加剧的不安。
最后,一整本书在2012年6月被推出[18],它由机密文件和信件构成,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与教宗最为亲近的圈子。因此,泄露大部分文件的负责人很容易确定:令人遗憾的是,它所涉及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与教宗极为亲近的“管家”。这是一个极大的感情触动。犯罪者被逮捕并交付梵蒂冈法庭,这场审判将引起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被判处18个月监禁的罪犯最终得到教宗的赦免,教宗还将在圣诞节前夕亲自前去探望[19]。本笃十六世认为,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正义应该得到伸张,但随后他不顾自己的痛苦,行使了常驻在他心中的慈悲。
辞职及教会之母隐修院隐退生活
因此,这一事件也在2012年底前基本了结。2013年2月11日,在为确定奥特兰托殉难者列圣品日期而召开的枢密会议上,本笃十六世出人意料地再次发言,并用拉丁语宣读了他希望放弃教宗牧职的声明。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因为极少有人会对此有所准备:“在天主面前经过屡次反省后,我得出肯定的结论,即由于年迈,我的体力不再适合以相应的方式来履行伯多禄牧职”。
教宗简明地说,他感到“身心活力”俱减,使其无力“胜任受委托的牧职”,与此同时,他也考虑到教会管理的需求:“今日世界变化神速,并因来自为信仰生活极其重要的争端而处于动荡之中”。辞职是在“完全的自由”中做出的,宗座出缺期于2月28日晚上8时开始。
尽管人们对这一辞职及其动机用墨如泼地写下了很多文章,但究其根本这一举动很简单,本笃十六世提出的理由显而易见且全然在情理之中,这是在天主和教会面前一个伟大的责任感的体现。这是面对伯多禄服务至高要求的一种谦卑行为,也是一种开启教会法典中已经预设、但几个世纪以来未曾有人涉足的道路的勇气。在选举中产生的教宗和他的任期的确终生有效(ad vitam),但教宗任期未必要随着教宗的离世才算告终。
许多人认为,辞职这一“新事物”是一种“历史性”行为,特别清晰地揭示了本笃十六世的远见和伟大灵性,这一角度有助于对整个教宗任期进行更仔细的深度重读。
在复活节庆典活动之前,教会将拥有一位新教宗。辞职后的时间众所周知:为教会祈祷的时间,私下的个人接触,罕有的书面干预,最重要的是为与天主的相遇做准备。教宗方济各的友善与关怀,“荣休教宗”的谨慎与祈祷,使教会能够正确评价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情况,并真诚地享受基督徒兄弟关系的光辉典范。两位身着白衣的人物拥抱和共同祈祷的美丽画面,远比毫无根据、工具性地将本笃与方济各对立起来的企图更令人欣慰。
若瑟·拉青格的思想及教会服务视域在八十年间不断扩展,从他的家乡巴伐利亚到天涯海角,直至他的目光凝聚于耶稣迷人而神秘的仪容,直到与天主相遇的那一刻。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位蒙召继承伯多禄牧职的神学家的特点,他通过教导、圣事服务和生活的见证在信德中坚固他的弟兄们。
- J. Ratzinger, La mia vita,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05, 6. ↑
- 玛丽亚后来没有结婚,她为协助弟弟而倾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与他一同生活并辗转于各地,直到1991年,在约瑟夫的爱和感激的陪伴,于罗马安息主怀。格奥尔格也是一位司铎,他致力于圣乐并成为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少年唱诗班,即著名的雷根斯堡主教座堂麻雀(Regensburger Domspatzen)的指挥;他于2020年7月1日在雷根斯堡去世。 ↑
- Benedetto XVI, Ultime conversazioni, a cura di P. Seewald, Milano, Garzanti, 2016, 92. ↑
- 同上,96 s. ↑
- 所有这些贡献如今均已发表于《Opera Omnia》第7/1卷中。 ↑
- Benedetto XVI, Ultime conversazioni, cit., 149. ↑
- J. Ratzinger, Introduzione al Cristianesimo, Brescia, Queriniana, 122003, 46 s. ↑
- Benedetto XVI, Ultime conversazioni, cit., 217. ↑
- 同上,《关于取消对马歇尔·勒菲弗(Marcel Lefebvre)总主教祝圣的四位主教开除教籍的法令信函》,参见https://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it/letters/2009/documents/hf_ben-xvi_let_20090310_remissione-scomunica.html ↑
- 同上, Ultime conversazioni, cit., 180; 222. ↑
- Premessa a J. Ratzinger – Benedetto XVI, Gesù di Nazaret, Milano, Rizzoli, 2007, 20. ↑
- 第一卷有关耶稣的公共生活,于2007年出版;第二卷有关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于2011年出版;第三卷有关耶稣的童年,完成了三部曲,于2012年出版。最后一卷附有导言,这篇导言签署于2012年8月15日,正值教宗决定辞职的时候。 ↑
- Benedetto XVI, Ultime conversazioni, cit., 194. ↑
- 同上,Lettera ai vescovi della Chiesa cattolica…, cit. ↑
- 这仍然局限于少数特定团体(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且幸运地在不破坏与整个圣公会信仰关系的情况下实现,甚至同时以圣公会传统中需照旧保留的丰富礼仪和灵性元素滋养了公教团体。 ↑
- 本笃十六世,在德国联邦议会的讲话,2011年9月22日。 ↑
- 本笃在当选教宗伊始便迅速介入了基督军团创始人马谢尔(Marcial Maciel)令人震惊的案件,随后又着手处理了该宗教团体的情况,为他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净化教会作出了有利的证明。 ↑
- G. Nuzzi, Sua Santità. Le carte segrete di Benedetto XVI, Milano, Chiarelettere, 2012. ↑
- 法庭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犯罪者。另外,为了弄清梵蒂冈出现的紧张局势大背景,教宗任命了一个由三名枢机主教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审讯,最后向教宗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教宗又将该报告交给了他的继任者,但该报告将处于保密之中,它并未引起外在可见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