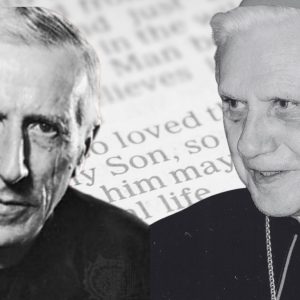我们正在举行“圣依纳爵年”为纪念这位罗耀拉的圣人皈依五百周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圣依纳爵的皈依是在1521年5月20日法国军队围攻潘普洛纳(Pamplona)城堡时,他遭到炮弹击中后养伤的那段时日。虽然当时的局势明显不利,但依纳爵为了维护国王的尊严,对他表示效忠,仍然戎马出战保卫城堡。由于圣依纳爵在他的自传中多次重复提到,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在皈依那段时期阅读了耶稣基督生平和圣人们的传记。这些书籍帮助他反省、祈祷和改变生活的决心。
关于圣人这段时期的生活,一般所谈的大都离不开这位负伤者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以及他个人与天主的关系。而本文愿意引发读者注意的则是权威者已研究过、但仍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也就是依纳爵在那段时期阅读的是什么书籍,而且是如何阅读的,因为这些对圣人的皈依和神修的陶成具有重大的影响。
嫂嫂玛达肋纳(Maddalena)的照顾
依纳爵负伤后,6月3日动身返乡,经过痛苦的旅程,于20日被抬在担架上抵达家门时,受到哥哥马丁·戛尔西亚(Martin Garçia)、嫂子玛达肋纳·德阿劳思(Maddalena de Araoz)和侄儿女的迎接。身为一家之主的哥哥通常在七月到九月期间住在乡下监督家业庶务,因此照料伤患的事应该都由嫂嫂和同样名叫玛达肋纳的大侄女两人来肩负。
嫂嫂玛达肋纳在依纳爵生命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1498年依纳爵二哥马丁迎娶玛达肋纳时,他们的母亲玛丽娜(Marina)业已过世,而大哥也在两年前死在战场,所以玛达肋纳俨然成为家中的女主人。当时依纳爵只有七岁,他留在家中直到十五岁才前往卡斯蒂利亚(Castiglia)的阿雷巴罗(Arévalo),在贵族胡安·贝拉斯格斯(don Juan Velázquez)府第继续接受教育。可见依纳爵少年时玛达肋纳即接替他已故的母亲照顾他,“赢得了他无法忘怀的信赖”[1]。当依纳爵在潘普洛纳受伤后决心放弃过去满怀激情、一心追求现世荣耀的这个过渡阶段,也正是这位嫂嫂在罗耀拉再度接纳、照料负伤的他。
玛达肋纳曾是西班牙著名的天主教女王依撒伯尔宫廷中的贵妇人,“深受女王宠幸,结婚时蒙女王赐赠珠宝和一幅美丽的圣母领报油画。为了这幅画玛达肋纳特别在居家城堡中建了一所小圣堂供悬挂,而依纳爵就经常在这幅画前祈祷”。“早在欧拉斯(Olaz)、阿兰萨苏(Aránzazu)和蒙色拉特(Montserrat)童贞圣母像之先,依纳爵已在家中这幅圣母像前形成了他对圣母的孝爱”。
当时依撒伯尔女王宫中有一位名叫盎博罗削·蒙德西诺(Ambrogio Montesino)的方济各会士从事翻译的工作。他是一位极受女王敬重且才华横溢的诗人,受女王之托将一部拉丁文古典宗教巨作翻译为卡斯蒂利亚文。这部大作是卡尔特隐修会会士萨克森尼亚的鲁道夫(Ludolfo di Sassania)所撰写的,名为《基督生平》,于1474年初版,并翻译成多种文字。蒙特西诺神父在1499年完成这部译作。
当时依撒伯尔女王的大资政方济各·希梅内斯·德·奇思内罗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也是一位方济各会士,担任托勒多(Toledo)的总主教、随后又获擢升为枢机。这位女王的资政创立了阿尔卡拉(Alcalá)大学及其著名的印刷厂。他为了庆祝这所印刷厂开工大吉,精美印制了蒙德西诺神父翻译的这套四册对开本的《基督生平》,并将之敬呈给信奉天主教的诸位君王。这套书于1502-1503年间问世,排版印刷均非常考究。随后几年,这所印刷厂又印制了非同寻常的多语言圣经合成本。《基督生平》书中凡是基督的话都以较大的字体和红色排印。蒙德西诺以当时“正在兴起的新帝国语言卡斯蒂利亚文翻译,符合华丽的哥特式[2]和依撒伯尔风格文体,段落逻辑结构繁缛。译作问世时俨然成为最具文艺复兴细腻优雅品味的典范”。依撒伯尔女王的做法促成这部大作在西班牙境内广受欢迎;同时,她也将这部作品赏给宫廷许多官宦。圣女大德兰也是这部译作的热心读者和推崇者。
因此,作为依撒伯尔女王宫中忠诚和备受宠爱的贵妇人玛达肋纳,自然而然在她的群书中,也包括萨克森尼亚的鲁道夫写的《基督生平》这套精美的大作,以及雅各伯·达瓦拉泽(Iacopo da Varazze)所写的《圣人传奇》(Legenda aurea 或Leyenda de los Santos)这部有关基督信仰的巨作。雨果·拉内(Hugo Rahner)神父说:“在天主教女王依撒伯尔宫廷中曾经看到西班牙宗教热忱振兴的玛达肋纳,把适于塑造人心的卡斯蒂利亚优美细致风格引入当时仍充满乡下和军人气息的罗耀拉”。
依纳爵经过腿部剧痛的手术之后,情况虽然良好,仍必须躺在床上疗养,于是要求看一些书来打发漫长难熬的时间。当时玛达肋纳有些书可以提供给依纳爵,即使与他的期望不同。可是她给依纳爵的建议不能等闲视之。这位夫人对依纳爵到底有什么影响见于日后圣人向一位比利时初学生叙述的一件小事:“他通常在一幅童贞圣母像前颂念日课经文,这幅圣母像美得令他想起玛达肋纳嫂嫂,以致令他祈祷分心。为了不再分心,他干脆用一张小纸条遮住了圣母像”。
年轻的依纳爵在阿雷巴罗、那赫拉及潘普洛纳时已经喜爱阅读。他在自传中说“他非常沉湎于阅读”[3]。他喜爱的读物是“骑士侠义文学”,“脑子里充满《阿马迪斯·德·高拉(Amadigi di Gaula)》和类似小说描述的那些东西”(依纳爵自传17)。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皈依后的依纳爵把他曾爱不释手的这类书定义为“世俗和虚幻的”。可是我们不能忘记《阿马迪斯·德·高拉》是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是骑士小说中最著名、最受重视的一部,它的卡斯蒂利亚文版在十六世纪初期非常普及,就连弗兰西斯哥一世(Francesco I)和卡洛五世(Carlo V)两位国王也喜爱,也深受塞万提斯(Cervantes)推崇,它启发了数个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灵感。书中固然弥漫着想象和爱情故事,却仍不乏崇高的品德理想和勇毅的精神,以及“受封为骑士前夕的彻夜祈祷”等等。总之,依纳爵热爱阅读的绝非庸俗或不足挂齿的书籍。
如今,蒙德西诺这位“语言艺术家以其擅于表达的能力和创塑力,把鲁道夫和教父们的拉丁文著作翻译成如诗如歌、令人想起骑士小说优美风格的散文”[4]。至于《圣人传奇(Leyenda de los Santos)》一书,伯多禄·德·勒杜利亚(Pedro de Leturia)神父则引用阿拉贡(Aragón)的熙笃会会士、曾是天主教费尔南多国王宫廷著名的军官瓜尔贝托·德·巴戛特(Gualberto de Vagad)为该书写的序言强调:“不能不说这本书的文词和风格具有某种程度的骑士和军人韵味,以致我们的依纳爵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想象手中拿的是一本服侍天主神圣事业的‘阿马迪斯’骑士小说”。瓜尔贝托这位隐修士视基督为“天主众骑士之王”[5]!
总之,依纳爵是个苛求的读者。他的嫂嫂玛达肋纳给的虽非他原本想要的书籍,但她也完全知道依纳爵渴望的是什么,所以她的回应绝非偶然:她给依纳爵两册新近出版的有关基督信仰生活的精美典籍,这两套书以日常用语精美编辑而成,很适合疗养中的这位“骑士”阅读。
依纳爵于是开始展读。这一读竟成了他走上皈依之路的开端。毛里吉奥·科斯达(Maorizio Costa)神父在他广泛评注依纳爵《自传》中指出:“显然地,依纳爵在阅读《基督生平》和《圣人传奇》之前并无任何开始皈依的迹象”[6]。
萨克森尼亚的鲁道夫的《基督生平》
鲁道夫究竟是谁?他是依纳爵前两个世纪的人。1295年出生,十八岁进入道明会,1340年转入斯特拉斯堡(Strasburgo)的卡尔特隐修会,在柯布连兹(Koblenz)的卡尔特隐修院当了两年院长,随之前往梅茵兹(Mainz),最后又回到斯特拉斯堡,于1377年逝于当地。《基督生平》一书是他最负盛名的旷世之作,以拉丁文写成。负责于最著名的印刷厂出版这部拉丁文大作的里格罗特(Rigollot)评论说:“圣多玛斯·阿奎诺从士林神学出发成功撰写了《神学大全》,鲁道夫则从四部福音及希腊和拉丁作家、特别是教父们的注释出发,以同样的结构和方式撰写了令人赞叹的《基督生平》”。鲁道夫对新旧约圣经的认识既深入又可靠,这从他在书中不断援引新、旧约圣经可见一斑;而引据的希腊和拉丁教父之多则令人叹为观止。瓦尔特·拜尔(Walter Baier)精准地分析了鲁道夫援引的教父言论,发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正确无误。可见鲁道夫执意尽其所知,把他当时可以考据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文献完全贡献出来了。
《基督生平》的序言告诉读者如何经由默观耶稣的一生来接近祂,进而爱祂,效法祂,追随祂。依纳爵将之视为珍宝。序言之后,全书分191章,行文流畅动人:“作者和他的时代给福音中的基督提供了人性和奥秘:《现代的虔诚》”[7]。在中世纪,手抄本的《基督生平》流通甚广,可能主要用于团体中大声朗读。印刷术发明后这部书广为流传,也供个人阅读和默想之用。据统计,此书到1880年为止共发行了九十版,翻译成多种文字。
深入认识圣依纳爵《神操》的人再回头来读《基督生平》,无不深受感动。许多人,包括耶稣会士,在景仰罗耀拉的圣人之余,咸认《神操》及其根源几乎是依纳爵灵修和神秘经验的特有成果。然而阅读鲁道夫的《基督生平》,当会发现它原来就是依纳爵神修经验源出的沃土,也因此更能了解《神操》的根源及其原始的贡献者。
从鲁道夫的书中我们发现他写作的方法:他先根据福音的记载来叙述事迹;接着反省和默想这些奥迹,直到沉浸其间,并使自己的生活符合福音“奥迹”的教导;再以向主耶稣基督做简短但充满热情的交谈式祈祷做结束。这样的祈祷通常称主耶稣基督为良善、温和、有耐心的。
显然地,依纳爵阅读鲁道夫的《基督生平》是他深入认识基督并与祂相会的主要途径。如此阅读引发他渴望效法基督,从而以有条不紊和内心参与的方法祈祷。这样的祈祷激发他联合运用记忆、想象、理智和意志,以充满热情及吻合福音、圣经、教父、乃至中世纪伟大神修家的神学和灵修知识,来“领会”基督的奥迹。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在依纳爵日后的灵修和文化经验中看到发展的痕迹。
一如保禄·索尔(Paul Shore)指出的,鲁道夫脑海中毫无神学争论的阴影:他的巨作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导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默观祂的奥迹和祂令人仰慕的人性,行文内容安详平实,完全符合教会伟大的传统。从鲁道夫的《基督生平》可以看出依纳爵灵修和神视的良好根基以及他“在教会内与教会同感”的亲切体验。依纳爵真正的对手是撒旦,而不是异端者。《神操》早源于“反宗教改革”之前[8]。
许多明确的议题都出现在鲁道夫的巨作中,之后又在依纳爵的“神操”中重现。我们在此仅能提出其中少许几个重要的。《基督生平》书中有一大章节专谈基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祂的母亲(参见《基督生平》II,70),但福音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这令人有些纳闷。可是依纳爵在《神操》第四周默想的开端竟隆重地提及(参见《神操》219-225),复在基督生平“奥迹”系列中再次谈到(参见《神操》299)。原来鲁道夫让我们了解,复活的基督显现给祂的母亲这个“奥迹”,乃是教父时代即有的古老信仰传统。因此依纳爵将之作为默观的对象。
另一件虽然不是那么重要却类似的事,就是鲁道夫书中亦提到复活的基督显现给阿黎玛特雅的若瑟(参见《基督生平》II,75;《神操》310)。依纳爵在《神操》第二周中建议我们思考“三种谦逊的方法”,以便更好地效法并服侍主耶稣(参见《神操》165-168)。但相关的事鲁道夫已在他书中耶稣在约旦河受洗那一章谈及,该章默想基督完美的谦逊(参见《基督生平》II,21,7)。另有完整的一章讨论“分辨”,即该书第二部分第41章,文中长篇论述“恶神”的诱惑,并指出五个“补救”之道;之后又谈到“灵修的人”所受的诱惑,同时列出十一个补救之道;最后也论述让“心思升入天主” 的十四个步骤。
依纳爵在某些“规则”中,特别是在“分辨神类”的表达方式上,就连遣词用字也几近鲁道夫。可见依纳爵不仅在祈祷“内容”上,也在精神生活的智慧上,经由鲁道夫而广泛承袭了教会的传统。
虽然我们不断发现依纳爵与鲁道夫相似之处和灵性上的接触,但这并不掩饰两人不同之处,不过这非本文探讨的对象。简而言之,依纳爵之有别于鲁道夫,其最特殊之处似乎在于鲁道夫尽其所能汇集了丰富的引据,流畅地给读者“说出一切”;而依纳爵则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他尽量减少话语,以便留出更多的空间,让祈祷的人直接与“奥迹”、与基督这个人、以及与天主在基督身上的作为相遇。他邀请人直接阅读和默想福音,不要浪费长时间在其他阅读中寻求“诸多学问”。我们还可以说,在中世纪,鲁道夫有脱离尘世现实事物的明显倾向,而依纳爵则因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历史时刻和环境,如何善用受造物和对世界的责任便成了他生活和《神操》中经常出现的重要议题。
雅各伯·达·瓦拉泽(Iacopo da Varazze)的《圣人传奇》
依纳爵的嫂嫂玛达肋纳推荐疗养中的他阅读的另一本书是风行全欧洲的名著,作者为1228年左右出生在意大利利古里亚海岸(costa ligure)城镇瓦拉泽(Varazze)的道明会士雅各伯·达·瓦拉泽。当时圣道明和圣方济各相继去世不久。他是圣多玛斯阿奎诺同时代的人,生逢瑞典及西西里国王费德里科二世(Federico II)与法国圣王路易九世(san Luigi IX)率领十字军最后几次东征时期,也是加达里(catari)异端之争时期,道明会士格外卷入这场争论。
雅各伯于1244年进入道明会,在1267至1286年间先后担任热那亚(Genova)道明会院院长及米兰(Milano)和博洛尼亚(Bologna)两会省省会长。随又蒙欧诺里奥四世(Onorio IV)和尼古拉九世(Nicola IX)两位教宗托付重大、艰困的使命。最后于1292年获任命为热那亚的总主教,在那动乱却极富活力时期肩负热那亚这个强盛海权共和国重要的牧灵和政治工作使命。1298年去世,五个世纪后,1816年由庇护七世(Pio VII)教宗列为真福。
雅各伯·达·瓦拉泽最著名的著作首次于1252至1265年间以拉丁文写成。虽有不同的书名,如《珍贵传奇(Legenda aurea)》或《菁英传奇(Flos Sanctorum)》,但最原始正确的乃是《圣人传奇(Legendae Sanctorum)》。这是整个中世纪最重要的一部圣人传记,保存了一千六百册以上的手抄本,可能仅次于圣经。1470年开始印刷拉丁文原本,到1501年估计已印行了七十至九十版。此外,又加上从书成后即有的许多翻译版本[9]。
我们必须了解清楚这部书的性质。它原是依循教会礼仪年历而撰写的圣人节日礼仪引言的汇集。作者雅各伯本人生前继续不断地予以修改或增加新的内容,如各地敬礼的圣人。也因此,随着时日而增加许多不同的版本,从原始版的178章逐渐增加到440章的版本,可见版本之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该著作的名称。拉丁文“legenda”这个字的意思仅是“必读之作”,而在此指的就是圣人。其实,书中收集的许多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圣人行传,从史实观点看不见得完全可靠,所以书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在今天看来乃属于“传说性质”。然而,该著作并不应因此而受到低估。就连“bollandisti”(译者注:十七世纪一群以历史文献和严谨态度编辑圣人行实的耶稣会士社团)的创始人简·博兰(Jean Bolland)也维护雅各伯的著作说:“我承认雅各伯的风格不比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更为正派,但他不仅是一位明智的圣人,也具有谨慎和极大的判断力”。
超越了这初步的印象之后,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圣人们的生平事迹并非信手拈来的,也不是依照它们在地方上的重要性或根据形式及文化类型来选取的,而是为了把圣人们的行传引回到教会的礼仪年内,将之建构成一支生活典范的巨柱。诸如:活在圣经中并与教会历史同行的宗徒;使人回忆帝国时代并推崇当时哲学家品行的殉道者;作者雅各伯时代希望提醒并确立的精修者,他们虽未流血致命却宣认了真理;那些生活在已非基督信仰的地区、在教会历史上传递思想价值或更新教会生活的隐修士;那些显示人具有无限的意志力,足以改变事态的娼妓;再就是证明圣德生活典范不只来自古圣先贤的现代或当代的圣人”[10]。
另有指出:没有这部巨作“就不可能了解许多宏伟主教座堂内外雕刻的象征意义。大部分这些建筑都用热那亚这位总主教所收集的美好描述和传奇来装饰:书中的故事和圣迹都绘画或雕刻在欧洲各主教座堂或大小教堂的祭台装饰屏或柱顶上。且不论这些艺术装饰品叙述的故事的真确性如何,它们都是解读这部书最好的途径”[11]。无论如何,书中的叙述非常引人入胜,俨然是一部把圣德的典范与人生的美好和悲哀维系在一起的杰作。养伤中的依纳爵渴望阅读小说,而雅各伯这部书所叙述的圣人史迹除了超凡和动人之外,更提供了不同方式的成圣芳表。
《圣人传奇》与鲁道夫的《基督生平》不同之处是其版本及版数之多,包括卡斯蒂利亚文版,使人无法确知传到养伤中的依纳爵手中的到底是哪个版本。但这并不重要。卡巴瑟斯神父于1521到1522年间在塞维利亚(Siviglia)出版了一部约三百页,但我们认为是六百页的珍贵完整手抄对开本。这个版本肯定非常接近依纳爵所捧读的。这使我们很能领会到依纳爵在他去世之前叙述的他阅读那本书的经过。依纳爵《自传》中的这几段话很著名:“的确,阅读我们的主和圣人们的一生时,令人不禁停下来思索:‘要是我做圣方济各和圣道明所做的,该会发生什么事?’…他的整个推理都在告诉自己:‘圣道明既然做了这个,那么我也要这么做;圣方济各做了这个,我也同样要做’”(《自传》7)。
众所熟悉的是,依纳爵“长时期”反省这些阅读而产生的内在反应如何引领他走上皈依之路:“不同的就在于:当他想到尘世的事就感到非常快乐,但由于疲累而丢开这些事之后,便又回到枯燥乏味、闷闷不乐之中;然而当他想到赤足到耶路撒冷朝圣,途中只吃些野菜,或做圣人们所做的种种刻苦时,不仅感到安慰,即便这些思维离开之后,仍然感到愉快和欣慰”(《自传》8)。
再者,依纳爵在回忆过去的生活而感到需要做补赎时便说:“到此,一股效法圣人的渴望就涌上心头,不管处境如何,只在乎期盼因着天主的恩宠而做圣人们所做的。然而他尤其渴望做的,乃是一旦痊愈便前往耶路撒冷”(《自传》9)。随即他又想到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该做什么,“好能持续不断地度补赎的生活”,比方“隐居在塞维利亚的卡尔特隐修院内,不显露任何身份,避免受重视,仅以野菜为生”(《自传》12)。他痊愈恢复体力后,即从罗耀拉动身,开始朝圣之旅,途中圣人们的榜样不断寓居在他的反省和想象中:“当他记起要做圣人们所做的某些补赎时,即打定主意完全效法他们的所做所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心思让他感到欣慰”(《自传》14)。
依纳爵在神修路上有所进展之后,发觉他初期效法圣人的重大渴望仍过于“外在”,反倒应该将之内在化,使之稳健中庸一些:“他的整个意向集中在表面上把这些事情做大,因为他以为圣人们就是为了光荣天主而这么做的,却不考虑到其他更特殊的环境状况”(《自传》14)。
无论如何,《圣人传奇》对依纳爵的冲击显然非常重大,不仅在罗耀拉的那段时日,在往后的日子里也一样。在此我们仅举出几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圣方济各和圣道明的传记。忏悔的依纳爵在蒙色拉特时效法圣道明,决意每天自行鞭笞三次,搭船旅行时身上不带分文。他也效法圣方济各,丢弃所有华美的衣裳,身上只套一件穷人的衣物。圣奥诺弗里奥(Sant´Onofrio)忏悔生活的故事也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圣人长发不修边幅,仅以海枣和野菜果腹[12]。
中世纪典型的神修之举是苦行朝圣耶路撒冷并留居在那里,圣阿雷西奥(Sant´Alessio)即如此做了。在谈到圣若亚敬和圣亚纳的生活时,书中有一处深深打动依纳爵,以致他一字不差地录入《神操》关于如何行哀矜的第七条规则结尾里:“我们有圣若亚敬和圣亚纳的榜样,他们把自己的财物分为三部分使用,第一部分给穷人,第二部分为圣殿的司祭职务和工作之用,第三部分留为自己和家庭之需”(《神操》344)。
《圣人传奇》在谈到法国圣王路易的生活时,也提及他的十字军东征之举。我们或许在《神操》默想“国王募兵”这件事中,听到依纳爵对此召唤的回应。在耶稣升天瞻礼礼仪引言中,谈到耶稣临升天之前在橄榄山留下的脚印。这个脚印令依纳爵充满兴趣之大,成了他告别耶路撒冷前夕那件著名事迹的核心。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谈这些事情,但没有这个必要:丰富又精彩的圣人历史显然是依纳爵这位被耶稣征服的骑士寻找堪为效命的新君王的背景。
圣依纳爵如何阅读这些书?
除了上面所谈的之外,还有一方面值得我们探究。依纳爵并不满足于浏览别人给他的那些名著:他阅读之“用心”值得注意。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同时我们也愿意在此强调:“他多次读而再读那些书,有相当一段时间对其几乎爱不忍释”(《神操》6)。他初期经常分心,反复思索自问。虽然如此,仍然亦步亦趋地走在皈依的道路上,以致家人发现他内心有所改变。他“从不问自己的健康状况,只管继续阅读和抱持良好的意向”(《神操》11)。
依纳爵皈依初期经常分心,在效法圣人方面也很重视外表。过了这个阶段,他继续深入阅读和反省,并开始写些点滴:“由于他现在对那些书籍很感兴趣,因此想到把耶稣和圣人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扼要地记录下来。当他可以在家中开始走动的时候,便着手用心编写一本书,在光滑的横格纸张上用红颜色抄录耶稣的话,以蓝颜色写下圣母的话,由于他擅于誊写,所以字迹很美。他这本书四开本,约有三百张纸。他用一部分时间书写,另一部分时间则用来祈祷”(同前)。
依纳爵少年时就开始学习阅读和书写。可想而知,他在阿雷巴罗服侍卡斯蒂利亚王国司库、之后又在那赫拉(Nàjera)服侍纳巴拉(Navarra)的公爵总督时,一定比在军中学习过更多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因此不仅对文书资料很熟悉,而且也练习了书写,难怪他坦承自己擅于文字书写。事实上他写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书信。当我们看到他纸上的字迹时,不得不被它的优美和工整的字迹所动。就这样,他透过练习书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深入并有选择性的阅读,一如他自己说的知道在鲁道夫的巨作中选取“一些最主要的事物”。
不仅如此:在阿尔卡拉印行、以红颜色标出上主的话的《基督生平》精美版本,也引起他用多种色彩来书写的想法。他留意默想中不同人物的特质,用心把所选择的语句段落扼要地写在质量上乘的纸张上。从依纳爵所选择的这些人物可以看出他祈祷的方法和教育学乃是本着鉴赏、留意和注入的态度,朝精深的方向进行。他的阅读方式绝非草率浏览,更非表面肤浅。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他意志坚定、具恒心和有条不紊。凭着这些特质他仍能在不算年轻的时期勇敢地从事长时期和繁重的研读,从拉丁文入门开始到获取神学博士学位为止。依纳爵抄录的虽然只是“一些最主要的事物”,却也写满了“四开本”正反两面三百张纸。这非同小可。很可能他在动身朝圣时即随身携带这本手抄书,至少带到曼雷萨(在那里写出《神操》),甚至更远的地方。
结语
走笔至此应该做个总结。依纳爵是个热爱阅读的人,他受伤疗养时期为了打发时间,要来一些书籍阅读。他的嫂嫂玛达肋纳给他两部非同小可的著作,是十三世纪后两百年间欧洲基督文学上最重要和最畅销的两大作品。这两部书在西班牙几位天主教国王统治下,同时也在教会生活和文化欣欣向荣的几十年中,翻译成卡斯蒂利亚文出版发行;那是对开、巨大、印刷精美、极具分量、以优美和引人入胜的风格写成的两部杰作,依纳爵非放在膝上或桌上书架来阅读不可。
依纳爵开始展读这两部大作,他的生命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在书中遇到温良、吸引人、为他受难至死的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召唤他跟随祂。经由耶稣,依纳爵又和祂的母亲熟悉起来,遂开始步武圣人们芳踪,这些圣人以自己的理想、德行和英勇的行为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这两部书依纳爵一读再读,从中学习如何与耶稣、玛利亚和圣人们交谈。他把必须铭刻在脑海和心中的话、以及启发他立意效法的榜样都抄录下来。
上主继续不断引领依纳爵在人生旅途和灵修经验上前行,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愈加深入,效法圣人们的步伐也日益平衡和成熟,他的灵修教育学也因此更具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特性。依纳爵在罗耀拉养伤时期着手抄录的“大书”或许会在朝圣旅途中失落,但他在罗耀拉细读两部巨作的心得,对塑造他成为一个崭新的人,一位朝圣者、《神操》的作者、新的修会生活方式的创始人,必定具有决定性和持久的影响。如今,在天主教会内,从基督信仰传统的古老宝藏中诞生了一种新神修,这将给教会日后的使命带来新的活力和冲劲。
- 本文关于玛达肋纳·德阿劳斯的引述见于H. Rahner, Ignazio di Loyola e le donne del suo tempo, Milano, Paoline, 1968, 185-187。 ↑
- E. del Río, Introducción a: Ludolfo de Sajonia, La Vida de Cristo, Madrid, Universidad de Comillas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0, VIII-IX. ↑
- Ignazio di Loyola, s., Autobiografia. Commento di Maurizio Costa, Roma, AdP, 2010, n. 5. Le citazioni dell’Autobiografia, con la numerazione classica, sono riportate direttamente nel testo dell’articolo. ↑
- E. del Río, Introducción a: Ludolfo de Sajonia…, cit., XIX. ↑
- 参见R. García-Villoslada, Sant’Ignazio di Loyola, Cinisello Balsamo (Mi), Paoline, 1990, 183 s; P. Leturia, «El “Reino de Cristo” y los prólogos del “Flos Sanctorum” de Loyola», in Estudios Ignacianos,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57, vol. II, 57-72. ↑
- Ignazio di Loyola, s., Autobiografia, cit., 46, nota 24. ↑
- E. del Río, Introducción a: Ludolfo de Sajonia…, cit., XII. Alla Vita di Cristo di Ludolfo è stato già dedicato un articolo su questa rivista: E. Cattaneo, «Il Natale con Ignazio di Loyola, lettore della “Vita Christi”», in Civ. Catt. 2020 IV 456-463, con ampie citazioni del capitolo sulla Natività. Sul rapporto fra la Vita di Ludolfo e il testo degli Esercizi, cfr R. García Mateo, El misterio de la vida de Cristo en los Ejercicios ignacianos y en el Vita Christi Cartujano. Antología de textos, Madrid, BAC, 2002. ↑
- 参见 P. Shore, «The “Vita Christi” of Ludolph of Saxon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Ignatius of Loyola», i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30 (1998/1) 17. ↑
- Per quanto riguarda l’opera di Iacopo da Varazze, facciamo ampio uso di F. J. Cabasés, «Introduzione», in Beato Iacopo da Varazze O.P., Leyenda de los Santos, Madrid, Comillas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07, VII-XCII. L’edizione critica è: Iacopo da Varazze, Legenda aurea, a cura di G. P. Maggioni, Tavernuzze (Fi), Sismel – Edizioni del Galluzzo, 19982. ↑
- «Presentazione» della versione italiana di Jacopo da Varazze, Legenda aurea, a cura di A. e L. Vitale Brovarone, Torino, Einaudi, 20072. ↑
- F. J. Cabasés, «Introduzione», cit., XVII e XIX. ↑
- P. Leturia, «El influjo de San Onofre en San Ignacio a base de un texto de Nadal», in Estudios Ignacianos, cit., vol. I, 97-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