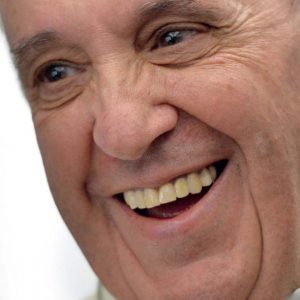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出其不意地打击了世界各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同时揭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政策及措施的缺乏,世界上存在的极大不公平,以及全球公共卫生战略性合作的不足[1]。病毒无形地威胁着人们的安定生活,令人惶惶不安,不知所措。一方面,我们顿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从卫生系统崩溃、经济下滑、工作不稳定,到个人习惯的改变和保持社会距离的规范,整个世界被紧紧地笼罩于一种不确定性的阴霾中,死亡的阴影似乎离我们仅有咫尺之遥。
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是:难道不确定性真的是此次大流行病带来的新生事物?还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了固有的状况?换句话说,当前势不可挡的不确定性打破了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保障,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还是应归咎于我们长期以来的疏忽大意?另外,这种以概括性术语描述的情况是否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都具有相同的不确定性?以上提问要求跨学科的解答,也正是本文关注的对象。
首先,让我们着眼于展开论述的前提。我们必须认识到,实际上,地球上的许多居民早已长期处于由贫困、边缘化、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中,这种”常态”持续的时间已经过于漫长。其次,”流动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多重性,使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一种持续的不确定状态之中。也就是说,当今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健康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适合扎根发芽的沃土。换句话说,病毒并非当前唯一的罪魁祸首,为了走出这一健康危机,我们必须追根究底,认清当前不确定性的多样性以及滋养和促进这些不确定性的社会结构。
已有的贫困状况
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健康状况不佳的人造成的风险极高,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但是,贫困是临床因素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影响着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2]。在社会援助和基本服务匮乏的地方,脆弱性[3]有所增加,死亡和不确定性是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威胁。病毒的到来使数百万人已有的贫困状况愈加恶化,并同时极大地助长了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以下的联合国数据揭示了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的巨大不确定性:”贫困不仅是单纯的维持生活、低收入和资源不足,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包括饥饿、营养不良、缺少得体的住房、缺乏享受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机会、遭受社会歧视和排斥、不得参与决策过程,等等。2015年,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超过了7.36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0%,他们在痛苦中挣扎,无法满足健康、教育、水、卫生设施等基本生活需求。在25-34岁的年龄段中,贫困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是100:122。预计在2030年以内,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儿童将有可能超过1.6亿”[4]。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来说,不确定性并不是一种新体验。那些无法摆脱贫困的人长期生活于不确定性的煎熬中,其根本原因并非身体缺陷或是基本社会结构的脆弱性,而是边缘化、不稳定和排斥的结构[5]剥夺了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机会[6]。新冠病毒只是加剧了已存在的固有问题。
对此,另一份联合国文件指出:”大流行病正在突显和加深已存在的不平等,同时也暴露了社会、政治、经济和生物多样性系统的脆弱性;反过来,这些因素也在加重大流行病的冲击”[7]。也就是说,大流行病、排斥和边缘化形成了一种致命的恶性循环,打破了穷人对有尊严的未来的梦想。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对数百万人来说,并非新冠病毒导致了不确定状态,而只是凸显了它的存在。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随之而来的疑问是:是否所有人都能摆脱整个人类面临的不确定现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本能地倾向于一个否定的答案。这并非出于单纯的悲观情绪,也不是因为我们已被大流行病拖得疲惫不堪,可以说,真正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贫困人口的现状推测,为大众所感知的普遍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根源和后果,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文化,解决方案必然有所不同。其次,虽然许多健康危机早已长期肆虐于”南半球”国家,例如疟疾、登革热、霍乱、埃博拉、寨卡病毒、艾滋病毒等等,但目前的健康危机则与之大不相同,它侵袭了所有发达国家,其严重危害使我们的反思有别于以往,不确定性的焦点超越了边缘化、社会排斥、贫穷和不稳定的层面。对此,教宗方济各指出:”新冠危机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冲击了整个人类。它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可见性”[8]。
由以上原因得出的推断是:走出危机的共同解决方案应以对不确定性因素的亲身经历和”认识上的多样性”为出发点[9],并在此基础上以跨学科和多维度的观点分析形势和采纳可行建议。因此,仅靠有效的疫苗、肺部呼吸器或对病毒影响的医疗监测无法根除当前的危机,简单的恢复常态也同样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恢复常态”便意味着对导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置若罔闻,继续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遗弃于不确定状态。
因此,若想根据认识论的多样性来审视现实,我们必须研究”流动的现代性”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动态,从中体察如何理解和应对不可预知的突变,比如当前困扰着我们的疫情。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是:哪些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流动的现代性”:不确定性的攀升
应该肯定的是,如同人类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当代文化中也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因此,对导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加以追究,这并不意味着将其归咎为当代的唯一特征,而是说在目前的大流行危机中,这些特征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意义重大,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首先,从人类学角度出发,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普吉特(Janine Puget)的解释将有助于我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他指出:”每个主体的自我思考都需要建立在一致性、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并以此为自我防护,以免受’陌生人’及其相关的不可预测性的侵害。在与自身及他人的关系中,主体为了应对和承受日常生活中的多种情况,会对确定性、真理和知识的感知产生依赖。[……]在多数情况下,化为泡影的确定性并不总是令人无法承受,失去的确定性常常会被另一个新的假象所取代。但在某些情况下,幻想成空则会导致痛苦的心理体验,引起令人惶惶不安、痛苦不堪的焦灼或恐惧,造成各种不良反应”[10]。
根据普吉特关于确定性假象的反思,后现代人需要承受的巨大生存压力显而易见[11]:在以多元性为特点的生存条件下,主体需在缺乏外部帮助的情况下不断地构建自我身份[12]并维护个人的确定性。此外,在缺少传统和外部权威[13]为参照物的情况下,后现代人需要不断做出有安全系数的选择和决定。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种漫无目标的状态中进行:从碎片化的时间[14],到碎片化的身份[15]和被淡忘的叙事[16]。在当代文化中,个人主义风行于世,现代人”以个人为解决方案,与制度进行抗衡”[17]。个人至上的唯我论以自主权、自决权和独立性为基本价值,不仅容易造成自我指涉,甚至有扭曲和异化人性的风险。简言之,当代文化强调个人至上,崇尚自给自足,但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恰恰滋长了它意欲抵制的不安全感。正如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所言:”所有为提高安全性而采取策略的原因,追根结底,是我们的典型生活模式中充满了不确定性”[18]。问题的关键是,发展个人自主权与现代性的设想和要求完全不符。因此,在实际生活中,自由及其具体形式下的行使存在着实质上的减少和妥协。
事实上,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个人都应生活在相遇[19]和社会性中[20],与他人同行,使生活成为可持续和卓有成效的经验;我们的某些特征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层面,比如相互关心[21]、信任[22]、同理心、团结互助和对话。推崇自给自足生活的文化主张有可能助长扭曲人性的行为,包括对别人的孤立、怀疑、卑鄙、漠不关心、偏见、蔑视、毫不妥协地保全自己、对别人的差异以暴力相对,等等[23]。
然而,对确定性的痴恋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具有包容性的确定性必须坚持对真理的探索,以相遇、对话和追求美善[24]为前提,否则,它将沦为以偏概全的绝对化,成为有利于宗派主义和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助长不确定性、恐怖和暴力的滋生。
另外,当代对我们的诱惑是通过无休止的消费来满足对确定性的渴望,其结果很可能是将购买力和自由、快乐经验的积累和生命意义混为一谈。对此,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商人大肆宣扬自己的产品,仿佛他们的服务和消费品具有神奇效应,可以战胜令人烦恼的不安和内心深处的威胁感”[25]。事实上,这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积累的问题,当今的广告具有典型的”个性化”[26]吸引力,以更大的强度将经验商品化,向顾客提供暂时的满足感,并以更强的方式不断刺激新的需求,开发成瘾型消费[27]。这种潜藏的冲动式享乐主义,贯穿于我们与事物和他人的关系中[28],将我们禁锢于个人的小天地中,终日被不断增长的不满吞噬。
最后,在”流动的现代性”特征中,另一个导致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是高度的不信任。其原因很明显:某些传统机构的瓦解造成社会的纲纪紊乱和骚动不宁[29]。当今世界中尤其自相矛盾的是,虽然我们拥有更多获取信息的可能,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却越来越严重[30]。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数据越多,相互的信任越少。
对此,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解释很有启发性:”在整个数字世界中,信任是一个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东西。当信息可以轻易地信手拈来时,信任便失去了意义。信息社会否定信任的存在,因为信任的前提是人际关系中的未知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信任’危机是由媒体造成的。高度的网络化信息收集已成为一种监控的形式,使信任在社会实践中越来越失去意义。也就是说,从结构上来说,透明的社会与监控的社会如出一辙。在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的地方,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实际上会转向监控和透明”[31]。
诚然,我们不应把社交网络妖魔化,但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健康的公共生活,我们必须增强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取舍[32]。在此,哲学可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如埃斯基罗尔(Esquirol)所言,批判性反思[33]必须伴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生活中的”无限意义”,它意味着”不可将人类生活简化为纯粹的验证或因果解释”[34]。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以信任为前提[35],与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截然相反。一旦对控制的需求和实施不断增长,怀疑和不信任必然会随之而来,并进而滋生不确定性和暴力[36]。当今的假新闻泛滥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动态,也是一个危险的社会病症,事实已多次证明,它可能会演绎为各种不包容、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行为,甚至发展为恐怖主义活动。
鉴于上述的文化动态以及引发其他情况的可能性,各社会成员和机构应及时行动,以避免普遍不确定性的进一步恶化。在这场健康危机中,我们不断强调”同舟共济”,”任何人都不能被遗弃”。那么,我们应怎样实现这种对统一和团结的期待?走出危机的保障又从何而来?
希望之光
不确定性在此次健康危机时期层出不穷,要求我们不断做出令人满意且持续性的回应。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上述不平等的存在,然后从中找出导致不确定性的机制。此外,穷人在应对日常生活不确定性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向他们取经。通过被边缘化群体的经验,我们归纳出以下三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希望能够有益于共建大流行病后的确定性。
首先是相互依存。穷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离开它等于无法生活。当今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高呼: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人际关系而独立生存,我们不应鼓吹自给自足,更不能以不人道的利己主义怂恿与世隔绝的独自生存。我们需要的是人性化和可持续的确定性,是承认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兄弟相待、团结一致、共同担当(参见《众位弟兄》第106条)。对这方面良好的实践可以使我们成为恢复社会纽带的动力。
第二,是以丰富的创意和想象寻求希望。面对日常的不确定性,社会中的被排斥者不应麻木不仁、消极被动地浪费时间,坐失良机。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我们必须积极行动,改善政治和经济体系,加强健康、教育、生态等方面的公共事务责任感。另外,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对以往的依恋,慎重决定何去何从:满足于恢复危机前的”常态”将无异于固步自封、重蹈覆辙。
最后,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脆弱性中团结互助,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脆弱性不仅意味着处于困境和有需求的状态,而且也是助人为乐的机会(参见《众位弟兄》第56-96条)。在这个世界里,偏见和怀疑筑起的高墙破坏了人天生就有的团结性,因此,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弱者,在大流行病各种形式的脆弱性中患难与共。恰恰是脆弱性敦促我们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各种威胁变得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在预防机制上达成一致,那么,应该用怎样的正义范式来指导各种关系?鼓吹过激的自给自足观念只会带来普遍的危害,我们需要认识到共同的脆弱性,开拓相遇和互信的道路,弘扬人文精神。
总而言之,为了抵制目前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来龙去脉,吸取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遗恨万年[37]。
- 这一切其实并不足为奇,埃博拉危机就是另一个最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Cfr. J. E. Stiglitz, La gran brecha. Quéhacer con lassociedadesdesiguales, Barcelona, Taurus, 2015, 207-209 (in it. La grande frattura. La disuguaglianza e i modi per sconfiggerla, Torino, Einaudi, 2015). 关于不平等对公共健康造成的影响:cfr. A. Deaton, El gran escape. Salud, riqueza y losorígenes de la desigualdad,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5, 123-147 (in it. La grande fuga. Salute, ricchezza e origini della disuguaglianza, Bologna, il Mulino, 2019); C. Peralta, «I filosofi del contagio. Come gli intellettuali hanno capito il Covid-19», in Civ. Catt. 2020 II 417-428. ↑
- 贫困的定义及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cfr. A. Cortina, Aporofobia, elrechazo al pobre. Un desafío para la democracia, Barcelona, Paidós, 2017, 125-137; S. Baker Collins, «An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from those who are poor», in Action Research 3 (2005/1) 9-31. ↑
- “我们可以将弱势人群分为两类:那些因其生存状况而具有脆弱性的人,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或身体健康因生活和工作的处所或方式而受到威胁的人;以及那些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而变得脆弱的人”(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Organization – Activities – Members, Switzerland, CIOMS, 1994, 26). ↑
- Onu, «Ending Poverty» (www.un.org/en/global-issues/ending-poverty). ↑
- “总体来讲贫困是生活不稳定的问题,脆弱的个人或群体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因物质的匮乏而无法保证社会和经济独立,可能会最终陷入我们所说的’被排斥”’(R. Castel, “Los riesgos de exclusión social en un contexto de incertidumbre”, in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Sociología 72 [2014/1] 17). ↑
- “贫困严重损害人们的福祉,带来不公正。 这种损害亦称结构性暴力,即通过贫困的条件和影响在远距离内施行的暴力。 陷入贫困的主体是最脆弱人群。 […]鉴于人类创造巨大财富和生产过剩资源的能力,贫穷是经济、政治和道德败坏的象征,是一种不应存在的不公正现象 (L. Watts – D. Hodgson,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Social Work: Cr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8). ↑
- Onu, «Shared Responsibility, Global Solidarity: Responding to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marzo 2020. ↑
- Francesco, Ritorniamo a sognare, Milano, Piemme, 2020, 9. ↑
- “弱势群体的生活经历决定于一种认识上的不公正,它实际上是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需求的置若罔闻。[……]脆弱性是全球健康领域中那些有权定义和否定影响与需求的人以及那些被定义和被否定的人之间的差距。大流行病正在呼吁我们加强对某些特定边缘化群体的关注,修复造成它们的脆弱性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历史断裂” (A. Ahmad et al.,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made vulnerable in the era of COVID-19?», in The Lancet, vol. 395, 9 maggio 2020, 1481 s). ↑
- J. Puget, «Quédifícil es pensar incertidumbre y perplejidad», in Revista de la APdeBA 24 (2002/1-2) 136. ↑
- “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是:压力、匆忙、痛苦、抑郁、挫折、焦虑、个人负担过重、持续的风险以及存在的失败——一种无尽的自咎”(G. Uríbarri Bilbao, La vivencia cristiana del tiempo,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2020, 13). ↑
- Cfr. F. Vidal, La última modernidad. Guía para no perderseel siglo XXI, Santander, SalTerrae, 2018, 15. ↑
- Cfr. P. Bruckner, La tentación de la inocencia, Barcelona, Anagrama, 1999, 21 (in it. La tentazione dell’innocenza, Santa Maria Capua Vetere, Ipermedium Libri, 2001). ↑
- Cfr. Byung-Chul Han, La sociedad de la transparencia, Barcelona, Herder, 2013, 62 (in it. La società della trasparenza, Milano, nottetempo, 2014). ↑
- Cfr. Id., El aroma del tiempo. Un ensayofilosóficosobreel arte de demorarse, Barcelona, Herder, 2015, 9 s (in it. Il profumo del tempo. L’arte di indugiare sulle cose,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17). ↑
- Cfr. F. J. AlarcosMartínez, «Religión y ética ante la incertidumbre», in Id. (ed.), Religión, espiritualidad y ética para tiempos de incertidumbre, Madrid, PPC, 2013, 32 s. ↑
- U.Beck – E. Beck-Gernsheim, La individualización.El individualismo institucionalizado y sus consecuencias sociales y políticas, Barcelona, Paidós, 2003, 31. ↑
- N.Luhmann, “El concepto de riesgo”, in J. Beriain (ed.), Las consecuencias perversas de la modernidad, Barcelona, Anthropos, 1996, 150. ↑
- 这个想法在教宗方济各的训导中尤其突出。可参见《福音的喜乐》,第220条;《生活的基督》,第169条,第183条,第222条;《众位弟兄》,第30条,第47-48条。 ↑
- “我们自古相互依存,这种关系是人类的基本特性,即使个人主义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普遍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否认这种互惠性”(J. Butler, Sin miedo.Formas de resistencia a la violencia de hoy, Barcelona, Taurus, 2020, 60). ↑
- Cfr. E. Kittay,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 Cfr. A. Giddens, Consecuencias de la modernidad, Madrid, Alianza, 1994, 40 (in it. Le conseguenze della modernità. Fiducia e rischio, sicurezza e pericolo, Bologna, il Mulino, 1994). ↑
- “正因为明知应该进化,所以目睹现实中各种各样的退化形式尤其使我们不安。以暴力为例,它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涉及范围也极广:从最令人发指的谋杀和最残暴的恐吓,到无数公开或隐藏的不公正和冷漠”(J. M. Esquirol, La penúltima bondad. Ensayo sobre la vida humana, Barcelona, Acantilado, 2018, 4; corsivi dell’autore; in it. La penultima bontà. Saggio sulla vita umana,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19). ↑
- Cfr. J. L. Martínez, Conciencia, discernimiento y verdad,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Cristianos, 2019, 287-378. ↑
- Z. Bauman, Daños colaterales. Desigualdades sociales en la era global,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1, 24 (in it. Danni collaterali. Diseguaglianze sociali nell’età globale, Roma – Bari, Laterza, 2014). ↑
- Cfr. G. Lipovetsky, Gustar y emocionar. Ensayosobre la sociedad de seducción, Barcelona, Anagrama, 2020, 264-266 (in it. Piacere e colpire. La società della seduzione,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19). ↑
- Cfr. Id., La felicidad paradójica. Ensayosobre la sociedad de hiperconsumo, Barcelona, Anagrama, 2008, 90 (in it. Una felicità paradossale. Sulla società dell’iperconsumo,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7). ↑
- “如今,爱情已沦为消费和享乐主义货架上的商品,没有人愿意接受其中的不利成分”(Byung-Chul Han, La agonía del Eros, Barcelona, Herder, 2014, 34 [in it. Eros in agonia, Milano, nottetempo, 2019]). ↑
- Cfr. U. Beck, «Teoría de la modernización reflexiva», in J. Beriain (ed.), Las consecuencias perversas de la modernidad, cit., 251. ↑
- 参阅:教宗方济各,通谕《众位弟兄》,第15条。 ↑
- Byung-Chul Han, En elenjambre, Barcelona, Herder, 2014, 99 (in it. Nello sciame. Visioni del digitale, Milano, nottetempo, 2015). ↑
- “早在1970年,阿尔文·托夫勒便在其《未来的冲击》中警告说,信息饱和可能会导致一种防御机制,也就是说,为了认识世界,人们将被迫将其简单化,而这种做法的风险是难免形成各种偏见”(M. García Aller, Lo imprevisible.Todo lo que la tecnología quiere and no puede controlar, Barcelona, Planeta, 2020, 19 s). ↑
- Cfr. J. M. Esquirol, Humano, máshumano. Una antropología de la herida infinita, Barcelona, Acantilado, 2021, 14 s. ↑
- Id., La penúltima bondad…, cit., 7. ↑
- “在不确定和多种选择的情况下,信任和风险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相信,信任是个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一个分解化机制和抽象系统的世界中,它也是增强独特性的关键。总的来说,信任与获得某种个体安全感有着直接联系” (A. Giddens, «Modernidad y Autoidentidad», in J. Beriain [ed.], Las consecuenciasperversas de la modernidad, Barcelona, Anthropos, 1996, 36). ↑
- 在心理学领域,非常有趣的是关于”无法忍受的不确定性”的研究。Cfr. M. González Rodríguez et al., «Adaptación española de la Escala de Intolerancia hacia la Incertidumbre: procesoscognitivos, ansiedad y depresión», in Psicología y salud 16 (2006/2) 219-233. ↑
- 本文摘自2021年4月13日至15日在马德里宗座科米亚斯大学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哲学研讨会《思考不确定性》(«Thinking the Incertitude»)上发表的一篇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