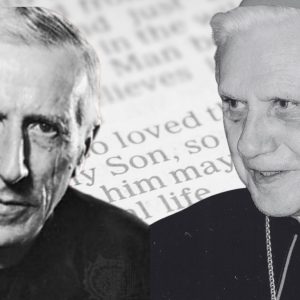爷爷和孙子共有唯一的一张桌子。/未来在此刻圆满 ……/我临在于未来的时代。/就像一个坐在马蹬上的男孩。(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生活,生活》)
如果圣经的信仰建立在历史中的天主的经验之上,吊诡的是希伯来语圣经中没有一个词的意思是“历史”,即经过渐进式的研究和记载的事件的进程。另一方面,圣经语言,有两个单词 tôledôt (世代),以及dôr(世代)——允许我们从更为内在的动态沿革来思考历史。下文[1]将描述圣经中对于这两个概念的交叉使用;不过,我们会先跑题一下,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看看。在新近的学术进程中,关于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现象,社会学,历史和心理学走了圣经早已开启的道路。对于那些仍然怀疑它的人,这里有对圣经在人类学问题上的洞见的肯定和确定。
这一圣经的双重范畴也是特别具有远见的历史神学的载体,其重要性尚未被重新发现。事实上,它暗藏着教宗方济各的思想和教导,关注贯穿历史的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他来说,就像上面引用的塔尔科夫斯基的诗一样,家庭和社会的餐桌汇集了所有的世代,在特定的时刻所共存的一切事物;对他而言,年龄最小者被召叫成为有远见的人,就像诗中的那个立足于马蹬上的小男孩。
一代又一代
首先,重要的是要考虑与“世代”一词相关的人类学现象。埃尔(Astrid Erll)的一篇特别具有启发性的随笔将指导这一探索[2],该研究与“文化记忆”现象有关。文章用以下几句话开头:“世代的概念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必不可少,却几乎未被关注。它构成了我们对家庭和社会,生物学和历史进程的理解的基础;同时,它虽倾向于以隐形的方式呈现,却是一系列的以无所不在的方式为基础的默认的假定”[3]。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埃尔(Erll)解释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区别。实际上,“世代”这一术语具有一个双重的语义价值:有时它指历时轴(跨越时间的世代),有时指共时轴(在时间的某个点上的世代组)。文化和人文科学在其古代和现代的演化中,实际上已经优先使用了第一个轴线,但是最近它们也开始关注第二个轴线的重要性了。
历时性的世代
在第一个意义上,“世代”一词是指人类在时间流淌中的生育繁衍。在这一历时和“垂直性”的意义上,该词涉及借由孩子的出生而得以延续的每个家庭群体。埃尔补充道,这个含义很古老,与人类一样古老。例如,关于起源(谱系)的论述可以在《奥德赛》的泰特马丘斯和雅典娜的对话中发现。泰勒马丘斯对督促他寻找父亲的女神雅典娜说:“我的母亲说我是她的儿子,但我不知道;没有人能知道是谁生了他”(《奥德赛》,第一卷,第215-216页)。据雅典娜观察,他的回答中并非没有失望:“事实上,很少有孩子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多数人比他们的父亲更糟,只有少数比他们的父亲更好”(《奥德赛》,第二卷,第276-277页)。
在现时代, 家谱关系已经成为批判性思维的金矿,从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开始:俄狄浦斯 (Edipo)和乔卡斯塔(Giocasta)情结(仅保留在希腊语中)都与生育有关,如今已成为我们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且增加了对创伤研究(Trauma Studies)的贡献,该研究以创伤经历沿着家谱系的传播为特征。研究表明,第一代和第三代较之第二代更能表达创伤[4]。孩子们常常对父母遭受的创伤保持沉默,而孙子们则对祖父母的创伤经历表现出兴趣和同情心。
在迁移现象中可见类似的现象。不同于移民的子女融入有别于父母本土文化的新文化,孙辈反而对祖父母的原籍文化表现出兴趣[5]。在古代诗歌,史诗和戏剧性思想中,就像在人类科学思想中一样,垂直世代一直是反思,象征或批判的对象。
共时性的世代
另一方面,埃尔继续说,“世代”一词的另一含义已有发展:这一含义不再是垂直的,而是水平的,指世代群。在人文科学中,对世代身份的关注相对较新。对“世代”一词的使用,或许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
“将1914年视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代概念出现的起点并不夸张。原因之一是,战争引发‘战争一代’概念的出现,抑或,根据沃尔(Robert Wohl)有影响力的书的书名,‘1914年的一代’。战后,一些欧洲国家的退伍军人为他们冠上‘遗失的一代 (lost generation)’的污名。他们指的是死于史无前例的机械大屠杀中的大量年轻士兵,也指他们幻想破灭的战争经历,以及在前线度过了成年初始的大量时光后难以在社会中重新找到他们的角色”[6]。
战后,理论性的反思一直在持续,其中1928年曼海姆(Karl Mannheim)出版的论著《世代的问题》(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堪称经典。曼海姆认为,“连贯的一代”[7]是由“社会——历史共同体”[8]的“共同参与”构成。然后,这里讲的是一个年龄组(Age Cohort),这个年龄组具有特殊的历史处境和特别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受教育的年份(青年时期和成年早期),这个群体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世代”。历史上的“几代人”尤其是由共同的创伤事件构成,例如战争失败或被迫移民。现在,“世代”的使用已变得无处不在:我们谈论“犹太屠杀(Shoah)的世代”,“婴儿潮的一代”(出生于1945年至1964年之间),“1968年的世代”,以及最近所说的“X世代”(紧随婴儿潮直至1980年),“Y时代”,也称千禧一代(直至1994年),Z代(直至2020年)和Alfa代(从2010年开始)。换句话说,共时性的世代的现象已然成为我们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圣经的先例
在这一点上,需要给与记忆以证实:代表人文科学相对较新的发展——“世代”和“世代”之间的差别——已是圣经思想的完整的构成部分。圣经甚至使用两个词来指示我们的“世代”一词。我们在此参考的是摩罗(Paola Mollo)的珍贵作品《旧约中世代变迁的主题》The Motif of Generational Change in the Old Testament(2016年)[9]。
作者写道,在《希伯来圣经》中,世代的概念表达出两种不同的意义:“族谱” (历时的)和“世代”(共时的)——用两个不同的词表示:“‘族谱(Genealogia)’和 ‘世代(generazione)’【……】圣经叙事中的这两个概念是绝对不同的,如同从同一希伯来文本中推论而出的,希伯来语的文本分别为两个词汇使用了各自不同的词根。在指“族谱”时,希伯来语主要使用的是术语tôledôt (תולדות), (而为了指“这一代是替代和革新的主角”时,则优先性地使用术语dôr (דור)。希伯来语中的这两个词词根不同,所以不会留有错误叠加概念的余地。希伯来语到希腊语的翻译(以及从希腊语到现代的印欧语),相反,消除了tôledôt 和 dôr 的差异,在此两种情况下,希腊语均选择了来自同根的*gen-, *gon-, *gn-的词汇。事实上,从词语索引中可以看出,希伯来语单词תולדות在(七十贤士本圣经)中更多被翻译为γενεσις (24 次) ,συγγενεια (14 次), 以及γενεα (1次)。至于דור这一单词,它几乎被专属地翻译为γενεα;也有一次是συγγενεια (依:38,12),4次为εκγονον (箴:30,11-14),这些术语也来自词根*gen-, *gon-, *gn-”[10]。
“这些是世代(tôledôt)”
圣经对世代族谱的纵向关系进行了特别清晰的反思,因此与tôledôt一词相关联,这来自《创世纪》的框架:“这些是……的世代”[11]。《创世纪》是一本关于生育的书:以孩子的孕育和出生(以撒格,雅各伯和厄撒乌,本雅明,培勒兹和则辣黑)为中心的家谱列表和故事交替出现。在《出谷纪》,《厄斯德拉上》,《厄斯德拉下》和《编年纪》中也可以找到家谱。如果这些是编辑学派(司祭传统)的鲜明标记,那么,它们也是宏观叙事历史的构成要素[12]。如前所述,圣经希伯来语中并未有一词指历史:历史是由 “世代tôledôt” 构成的,世代是历史的架构。
在《新约》中,《玛窦福音》(玛 1,1-17)和《路加福音》(路 3:23-38)的族谱列表都是耶稣的族谱。尽管从末世的层面而言,《新约》将世间压缩,一切都聚焦于一个“子”身上(“人子”和 “天父之子”),但它却从默西亚的角度,重新看待世代[13]。
在圣经中,不缺乏连接或面对连续的两代人(父亲,母亲和孩子)的情节和场景。几乎失明的依撒格问假扮成长子厄撒乌的雅各伯:“我儿,你是谁?”(创27:18)。“那时我为得到这孩子祈祷”,亚纳对司祭厄里说 (撒上1,27)。“孩子,我眼中的光!我看见你了!”当托比特又看到儿子时,感叹道(多11,13)。这些情节就是孩子的生命本身在受孕或幸存方面的情节,或是恩许,祝福,产业继承从一代传给另一代的情节。圣经中的天主与两代人的情节密切相连,祂在恢复“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玛3,24)中愿景中启示了自己。
该情节也可以扩展到三代。因此,在《创世纪》48:8-10中,若瑟把在埃及出生的孩子带到父亲面前;抑或,在女性版本《卢德传》4:16-17中,纳敖米怀抱卢德的儿子敖贝得, “纳敖米接过婴儿来,抱在怀中,做了他的保母” 。相反,《创世纪》50:23中,关于四代人的描述,被呈现于对若瑟一生的总结中: “若瑟见到了厄弗辣因的第三代子孙;默纳协的儿子玛基尔的儿子们,也都生在若瑟的膝下” 。在约伯的财产恢复原状后,他的故事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以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岁,见了他的儿子、孙子,直到第四代。约伯寿高年老,已享天年,遂与世长辞” (约 42:16-17)。
这些涉及两代,三代或四代的故事使我们能够理解一个非凡的神学图景:在十诫中,天主将自己描述为一个 “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的天主(出20:6);参见出34:7;民14:18;申5:9)。此问题的关键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学的。在他的一生中,一个人可以见证三到四代,看到他孩子的子女,也许还有后者的孩子。换句话说,从严格的道德角度来看,他将见证自己的选择,尤其是错误选择的影响,直至第三代或第四代。这就是天主 “审视” 和处罚的地方,为此采取行动。因此,该神学思想具有警告的价值,使人在自己的选择中面对责任:后果将由他的孩子,孙子和曾孙承担,而他本人将见证这一切。通过这种方式,圣经将天主的奥秘与道德生活的基本维度相连——它跨世代的维度。这展示了在历史的历时性中,对人类的“繁育” (generare)所带来影响的敏锐感知。
“这一世代 (dôr)”
圣经通过引历史和道德意义上的dôr一词,在另一代世代轴——当代这一代的“水平”轴方面展现出同等的专业知识。“世代”一词在道德意义上以《创世纪》6,9的洪水故事引入圣经的剧情中,“诺厄是他同时代(字面意思是:在他的世代)惟一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天主自己在创7:1中重申了叙述者的断言:“上主对诺厄说:‘你和你全家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一世代,我看只有你在我面前正义’”。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世代中的不同群体的身份;这是一种道德身份。
在她的著作中,摩罗着眼于与所讨论的“世代”有关的原因:世代变革的原因。在圣经中,这是一个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世代群体以如此多的“人物”的形式出现,这些人物以其性格和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角色为标记。我们已经提及了诺厄的同一世代,即洪水世代(创 6:9和7:1)。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出谷纪》(谷1:6-8)的开篇:“若瑟和他的众弟兄,以及这一代(dôr)死了以后,以色列的子孙生育繁殖,数目增多,极其强盛,布满了那地。有位不认识若瑟的新王兴起,统治了埃及” 。
在《出谷纪》和《肋未纪》后,《户籍纪》将所讨论的主题作为其交织的支点。这本书将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过度“戏剧化”:从经历出埃及,启示和西乃盟约的一代,到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代。在这一过程中,两代之间的接力并非是以简单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上,《户籍纪》所讲述的是,第一代作为见证者和有着诸多好处的受益者是如何被取消资格的,最终被判罪而在旷野中徘徊40年:直至这一代全部死去。实际上,出埃及的一代在《户籍纪》13-14中的12位探险家的事件中就名誉扫地了。当时,蔑视的态度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叛教,且不相信天主将把应许之地当作礼物赐予他们。由此,神圣的判决是:“这些【换句话说: “这一代” 】见了我的荣耀,见了我在埃及和旷野里所行的神迹的人,已十次试探了我,不听我的声音,他们决不能见我对他们祖先誓许的地方;凡轻慢我的人,决不会见到那地方[14]。【……】至于你们的幼童,你们曾说他们要当战利品的,我要领他们进去,使他们享受你们所轻视的地方” 。(户 14:22-23:31)。世代之变的原因可参见《民长纪》2:8-10,若苏厄的死亡以及他的世代的消逝: “上主的仆人,农的儿子若苏厄一百一十岁去了世。【……】当那一代人(dôr)都归于他们的祖先以后,在他们之后,兴起了另一代,他们不认识上主,也不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迹。”
因此,希伯来圣经中戏剧化了四个世代间的沿革,这些变化与诺厄、若瑟、梅瑟(围绕在西乃山的启示和盟约)和若苏厄这些人物紧密关联。根据风格,类比和对照的重复,摩罗在论题中确定了两种范例:“重生”(rigenerativo)(《创世纪》6-9和《户籍纪》13-14),其中一个(诺厄)或两个(若苏厄和加肋布)人物以他们的虔敬与邪恶一代(dôr)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堕落(degenerativo)(《出谷纪》1以及《民长纪》2),其中世代(dôr)的首领(若瑟,若苏厄)和他们同一世代的人死后,出现了新的人物——埃及有了新的统治者,以色列有了新的一代——,他们以无知为特征,即“无认知”,表征了这一民族生活的恶化[15]。
然而,只有能够宏观看待圣经的读者才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点。在被《民长纪》2:10 和3:2的取用后,dôr一词从圣经历史叙事的词汇中完全消失了,除了唯一的一处例外,即《编年纪上》16:15。事实上,《民长纪》后,圣经中出现了新的历史和道德主角:犹大和以色列的国王。历史的审判将落在他们身上。摩罗写道:“直到整个民长世代,人们所负的责任取决于他们作为集合体的表现和选择,而随后,君王成了承担责任的唯一主体”[16]。倘若过去的世代整体表现为伦理性的主体,那么现在王室成员——包括依则贝尔和阿塔里雅——则变成了历史评判的试金石。在这一人格化的世代与凸显的人物之间的相互交织(chassé-croisé)中,人们对历史以及对群体和个人所能扮演的互补或交替的角色有了深度的思考。
“世世代代”
贯通《旧约》的进程汇集为一个重要的现象:两个世代轴——族谱的垂直轴和世代群体的水平轴——在“代代相传”和“历经你们的世代”的表述中关联起来。这一双重表达模式将每个相同时代群体的角色转化为继承的经验,这些经验作为一种传统贯穿整个历史。由此,《圣咏集》79,13中写道:“这样做你子民做你牧场羊群的我们,能永远称谢你,能世世代代宣扬你的光荣”。这一表达经常出现在《圣咏集》中(参见:咏10:6; 33:11; 49:12; 77:9; 85:6; 89:2; 102:13; 106:31; 119:90; 135:13; 145:4; 146:10)。他们还出现在叙述和礼仪的语境中。例如,创17:12中说:“你们中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在生后八日都应受割损”(参见:谷12:17)。
“代代相传”的传承和对法律的遵守是圣经信仰的核心。这一传统不仅是纵向的,历时的,从父母到子女的,而且还涉及后来属于同一时代的各群体,因为他们应将传统付诸实行。天主的启示在每一世代对天主的初始经验中得以再次现实化,父母与祖辈之间的继往开来如同生命,生生不息。
新约中的“世代”
有必要指出的是,《民长纪》中消失的“世代”的范畴,却在《新约》中不断重现。此处,只需要引用《玛窦福音》中耶稣的两个确证:“我可把这一世代比作什么呢?它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玛11:16-19)。“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它其他的征兆。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世代起来,而定他们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听撒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 (玛12:39-42)。
让我们首先观察一下耶稣在这里如何讲解经文。当他斥责“这个世代”或“这个邪恶的世代”时,使人忆起《户籍纪》和《申命纪》中的天主和梅瑟,将旷野中的一代称为“邪恶的一代”,因为他们拒绝了“即将到手”的应许之地的恩赐(参见:申1:35;户32:13;14:35)。
在类似的场合中,圣经以‘天国的临近’来表现耶稣对这一世代的判决。耶稣在末世言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决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决不会过去” (玛24:34-35)。在后接的经文中,他以世代为关键词延续了他的思想,将洪水世代的黑暗与人子到来的见证人的黑暗结合起来(玛24:37-39)。
像诺厄的太古史一样,人子的末世轨迹也将表现出一个世代的其他优先选择。在基督面前,选择总是个人性的,这些选择在福音的画面中栩栩如生地临现:从黑洛德王到犹达斯,从第一个门徒到同耶稣一起被钉上十字架的盗贼,从富人到客纳罕妇人(sirofenicia)。福音本身还呈现出,面对天主的默西亚时,人选择善还是选择恶。面对福音的标记,他们做出的回应在影响着彼此。“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 (路1:65); “他的声誉遂即传遍了加里肋亚附近各处” (谷1:28):对耶稣的言语和标记的反对性的回应具有传染效力。
此外,我们应当观察到耶稣所使用的“这一世代”的表达具有特殊的价值:它可以传给能够阅读或听到福音的每一代人。耶稣当然是在所叙述的世界中向与他同在的那个世代讲话,但是,指示词的“这个”有能力超越叙事的边界能力,并到达每一个实践福音叙述的读者——听众那里。福音通过“这一世代”的表达传达到了每一代人——历史中的“现在”,“当前”,直至时间的尽头——每一世代都被要求在人子面前做出决定。
“所有世代的人都称我为有福”
除了回应天主的默西亚的责任外,另一种动力关涉历时和共时视角中的每一代人。路1:48b,在《谢主曲》中,玛利亚宣告: “今后所有世代(pasai hai geneai)都要称我有福(makariousin)” 。这句话呼应了她的表姐依撒伯尔,她在先地用过makarios一词,即 “幸福,有福” : “那信了由上主传于她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路1,45)。
玛利亚用自己的话呼应了犹太人历史上的另一个姐姐,即祖母肋阿。在她的儿子阿协尔诞生时(ʾāshēr, 含义为“幸福的,有福的”),她欢呼:kîʾishshĕrûnî bānôt, “因为女儿们都要以我为有福”(创30:13)。七十贤士圣经将这一希伯来语的表达翻译为makarizousin me hai gynaikes,“因为女人们都要以我为有福”,引出动词makarizō (“认为或声称有福”),这被《路加福音》中的玛利亚重新引用。玛利亚将这一动词归于原初的主语:“今后万世万代(pasai hai geneai)都要称我有福”。七十贤士圣经中的gynaikes,“女人们”一词被玛利亚替换为geneai “世代”,将赞颂延续到未来。除此之外,在《路加福音》中,玛利亚通过所引入的变化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跨度:不再指涉当下之所是(“女人们称我…”),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所有世代将称我…”。玛利亚在时间中将“称…为有福”这一词普世化了。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创造的效果穿越了叙事时空的限度:事实上,玛利亚的预言会达致每个咏唱《谢主曲》(Magnificat)的世世代代。玛利亚的欢呼自然是向依撒伯尔所发,它首先在整个叙事的世界中回响,然而,它也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传达到未来世代中的每一代,他们将在宣讲或歌唱中将此赞歌加以实现。肋阿所讲的最初的这句话是以默西亚的方式在玛利亚的话中加以实现的,她使之普世化为“世世代代”,直至《圣咏集》作者所称的“最后的世代(dôr ʾaḥărôn)” (参见:咏 48,14;78,4;102,19)。直至时间(tôledôt)的终结,未来的世代(dôrôt)被召集于玛利亚的颂歌之中,即咏唱施洗者若翰和耶稣诞生的颂歌。
教宗方济各教导中的世代的框架
由于人类学的圣经学在人文科学的发现之前,所以圣经理所当然地呈现为人类学领域的鼻祖。通过“世代”和“世代”概念的相互作用,由此促使我们从历史的基本动态出发反思历史。人类学的观念伴随着一种神学思想:在每个盟约的前后,基督耶稣事件(出生,生命,死亡,复活)的前后,神的计划与世代的相传紧紧相连。此神学财富不只需要新的理论家,批评家和创作者来发掘,而更需要新的诗人和讲述者。
这种圣经的双重视角贯穿于教宗方济各的思想和教导之中。从他的宗座任期伊始,他就呼吁在世代之间,尤其是在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合作:“那些有爷爷奶奶在身旁的家庭是有福的!爷爷是两倍的父亲,奶奶是两倍的母亲”[17]。 “我是多么地希望教会以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新的拥抱带来的无限欢乐来挑战所谓的丢弃文化!”[18]教宗经常通过先知岳厄尔的经文来强调年轻人和年长者的这种亲密关系: “此后——上主的断语——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们和你们的女儿们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你们的青年要见神视” (岳3:1;参见宗 2:17)[19]。
正如方济各教宗以不同方式所提到的那样,人类学模式是三代人的模式[20],也是一个神学模式:《圣经》中的天主不是某个孤身一人祖先的天主,而是作为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即包括圣祖父们,圣祖母们以及他们子孙三代的天主。具有意义的模式是,三代人的模式再次以意味深长的方式出现在《新约》中:“我记得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保禄写给弟茂德,这信德首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依和你母亲欧尼刻的心中,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 (弟后 1:5)。信仰的传播与代际生活的信仰有着深厚紧密的关联,正如旧约书中以多种方式表明的那样: “世世代代应宣扬你的工程,世世代代应传述你的大能” (咏 145:4;参见 赛 10:2;12:26-27;13:14;申 4:9;6,7,20-25;咏 78:1-8[21])。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有讲述的恩赐和使命——家庭的故事,人类家庭的故事——注定要与圣经的故事相交并与其交织在一起。对基督的信仰的传播历验在诸多方面,在诸多的环境中且藉着诸多的渠道。教宗方济各凭借其勇敢与智慧,将其置于重中之重:这正是世代相传的生命 (参见:咏 78:3-4)。
这涉及生命和生存的问题,也是方济各教宗关注的核心,即另一个跨越时代的前沿性问题:“共同家园” 和人类家庭的未来。引用葡萄牙主教的话,他说: “【大地】是每一代人都借用,且必须移交给下一代的”[22]。生态问题在世代关系中占据首位。这与父母对未出生的孩子及成长中的孩子的密切关注有关。正如与滕伯格(Greta Thunberg)有关的 “气候大罢工” 这一代人所表现的那样,年轻一代以挑战成年人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自从《愿你受赞颂》问世以来,教宗方济各的劝导就已在考虑未来的世代在地球上生存的问题上略见雏形。
倘若方济各教宗是世代关系的拥护者,那么他也是呼吁各代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翁,且末让他人剥夺了自己的希望[23]。在这个意义上,以年轻人为对象的《生活的基督》宗座劝谕将此处的呼吁凸显,而《众位弟兄》通逾重述了同样的议题:“每一代人都必须继续自己的前代人的奋斗和成就,并带领它们达到更高的目标”[24]。教宗相信:每个男女,每个世代在自身内都拥有可以释放在人际关系中的,理智的,文化和精神上的新能量的潜能”[25],为此教宗备受鼓舞。在这方面,他与保禄六世教宗相互呼应。保禄六世在开启1975年圣周礼仪时对青年人的讲话如下: “你们是你们这一世代的主角; 你们不是被动受邀的观众,而是富有你们青春与创新特质的使命的参与者和实践者”[26]。
即将到来的世代
通过整理tôledôt (世代)和dôr (世代)这两个概念,圣经为人类学和历史思想提供了指南针。此外,它打开了一个历史神学领域尚待探索的视角。这个观点使我们回溯到诗人塔尔科夫斯基所看到的“立在马蹬上”的男孩,他对未来满腹期待。
关于未来的世代,我们必须说它具有不可估量的特权:那一世代的人将跻身在第二次降临的主身旁。在《希伯来书》中,最具有逾越意义的圣咏是圣咏22,且藉着复活后的主之口而再被宣讲:“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在集会中,我要赞扬你” (希 2:12;咏 22:23)。在圣咏中,这一宣讲以 “未来的世代” 为对象(咏 22:31),在最后的经文中的描述为 “下代人” (咏 22:32)。在《圣咏集》的其他段落中,此世代被他们命名为 “下一代” 或 “末代” (咏 48:14;78:4.6;102:19)。在基督徒的视角中,这一 “即将来临的” 一代是最接近即将来临的主的那一代。新生的儿子们和女儿们看着我们,并替我们展望未来,关于他们,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跻身于在光荣中归来的复活之主 “身旁” 的,而祂藉着他们眷顾了我们。
-
这些文字同时是对我们的文献“生育,为什么?一个圣经视角”的缩短和发展,Anthropotes 36 (2020) 第139-190页。 ↑
-
参见A. Erll, «Genera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Three Constellations of Generationality, Genealogy, and Memory»,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45 (2014) 385-409。 ↑
-
同上,第385页。 ↑
-
参见V. Aarons – A. L. Berger, Third-Generation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 Trauma, History, and Memory, Chicago,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
问题中的现象被称为“汉森法则”(Hansen’s Law),参见M. L. Hansen, 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 Rock Island, IL, Augustana Historical Society, 1938. ↑
-
A. Erll, «Generation…», 参见第386页。 参见R. Wohl, La generazione del 1914, Milano, Jaca Book, 1984. ↑
-
K. Mannheim,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 in Köln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Soziologie 7 (1928) 309 («Generationszusammenhang»). ↑
-
同上。 ↑
-
参见P. Mollo, The Motif of Generational Change in the Old Testament: A Literary and Lexicological Study, Lewiston, NY, Mellen, 2016. 这一著作将从意大利原文中被引用,可在网上获得, La «dôr» biblica ed il tema del ricambio generazionale. Studio lessicologico e letterario di un tòpos, Università di Pisa, 2014. ↑
-
同上,P. Mollo, The Motif of Generational Change in the Old Testament: A Literary and Lexicological Study, Lewiston, NY, Mellen, 2016, 第25页。 ↑
-
问题中的标题出现在书中有10次,5次中有两次波潮:《创世纪》2,4a; 5,1; 6,9; 10,1; 11,10 / 11,27; 25,12; 25,19; 36,1(9); 37,2. ↑
-
参见:J. L. Ska, «Le genealogie della Genesi e le risposte alle sfide della storia», in Id., Il cantiere del Pentateuco. 1. Problemi di composizione e di interpretazione, Bologna, EDB, 2013, 83-112. ↑
-
参见:J.-P. Sonnet, «De la généalogie au “Faites disciples” (Mt 28,19). Le livre de la génération de Jésus», in C. Focant – A. Wénin (edd.), Analyse narrative et Bible, Louvain, Peeters, 2005, 199-209. ↑
-
只有加肋布和若苏厄,以及认识到应许之地的礼物之美的探险家除外,参见:民:14,30;26,64-65. ↑
-
参见P. Mollo, The Motif…, cit., 第89-97页。 ↑
-
同上,123页。 ↑
-
Francesco, Incontro con gli anziani in piazza San Pietro, 28 settembre 2014. ↑
-
同上,Catechesi, 11 marzo 2015. ↑
-
同上., Esortazione apostolica post-sinodale Christus vivit (CV), 25 marzo 2019, n. 192; cfr Id., La saggezza del tempo. In dialogo con Papa Francesco sulle grandi questioni della vita, Venezia, Marsilio, 2018. ↑
-
参见:同上,Esortazione apostolica post-sinodale Amoris laetitia sull’amore nella famiglia, 19 marzo 2016, nn. 187-198. ↑
-
参见:同上,Lettera enciclica Lumen fidei sulla fede, 29 giugno 2013, nn. 12 e 38. ↑
-
同上,Lettera enciclica Laudato si’ sulla cura della casa comune (LS), 4 maggio 2015, n. 159; Id., Lettera enciclica Fratelli tutti sulla fraternità e l’amicizia sociale (FT), 3 ottobre 2020, n. 178 (援引葡萄牙主教团会议, Lettera pastorale Responsabilidade solidária pelo bem comum, 15 settembre 2003, 20). 也参见 LS 53; 159-162. ↑
-
尤其参见CV 15; 74.。 ↑
-
FT 8. ↑
-
FT 196; 也参见Francesco, 后主教团的宗座劝谕Evangelii gaudium, 24 novembre 2013, n. 122. ↑
-
Paolo VI, s., Omelia, «Dominica Palmarum», 23 marzo 1975. 关于世界之新和历史之新的导论,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著作Vita activa (1958)中写道,“唯一的可能性在于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的,随着他的诞生,他的独特性中带着一些新的东西” (H. Arendt, Vita activa. La condizione umana, Milano, Bompiani, 2017, 128)。 ↑